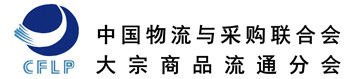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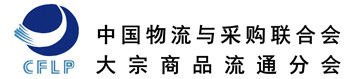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2021-02-04 来源:
政策空间的大小决定了未来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而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对市场主体的信心具有重要影响。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过程中,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政策空间不足,那么将会导致政策难以持续,进而打击企业家和居民等市场主体的信心,最终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简称“宏观政策”)难以较好地进行逆周期调节。2020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内外复杂环境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双发力,预计将会进一步压缩政策空间。与此同时,“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需要宏观政策继续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中央制定的重要目标,从而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正因如此,很有必要对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进行全面评估,从而为“十四五”期间的政策操作提供决策参考。
一、货币政策空间评价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进程仍然没有结束,本报告同时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指标评估货币政策空间的大小。与央行近年来操作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相一致,本报告将存款准备金率视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空间的主要测度指标,将利率视为价格型货币政策空间的主要测度指标。
第一,中国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由2018年初的14.9%降至2020年底的9.4%,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降准空间已经相对有限,不过面向大型金融机构的降准空间仍然相对充裕。
2020年央行采取了一轮全面降准操作和两轮定向降准操作,再加上前几年的降准操作,整个“十三五”期间央行已经累计采取了8轮全面降准操作和多轮定向降准操作。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各类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2018年初的14.9%降至2020年底的9.4%,降幅达5.5个百分点。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基准档水平已经从17%降至12.5%。不仅如此,超过4000家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从中国以往历史数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情况来看,6%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是比较低的水平。可见,“十四五”期间中国央行面向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降准空间已经相对有限,不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范围内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未来可以通过降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进行逆周期调节。
第二,中国的降息空间略有收窄,但是与美国、日本、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拥有较为充裕的降息空间。
结合“十三五”期间中国央行的政策操作实践以及2019年8月份改革后的LPR报价新机制可知,央行主要使用7天的OMO逆回购利率以及1年期的MLF利率两种政策利率进行降息操作。有鉴于此,本报告主要结合这两种政策利率水平的高低判断中国央行的降息空间。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7天OMO逆回购利率以及1年期MLF利率均有所下调。截至2020年末,两类政策利率都已经降至“十三五”时期的低位,由此可知央行在“十四五”期间的降息空间与“十三五”相比有所收窄。
不过,2020年美国、加拿大、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个经济体都大幅降低了政策利率。以美国为例,2020年3月3日和3月16日美联储分别降息50个和100个基点,一个月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50%—1.75%骤降至0%—0.25%,降幅达150个基点。加拿大、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隔夜或7天政策利率的降息幅度分别达到了150个、75个、100个、125个、175个百分点,平均降息幅度为125个基点。在多个经济体大幅降息的大环境下,中国央行降息的实际可操作空间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有所增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政策利率均已经降至零附近,这意味着它们的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货币政策彻底没有操作空间,因为还可以借助于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十四五”期间,中国央行同样可以考虑增加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前瞻性指引的使用,这样既能够节省常规货币政策空间以备不时之需,又能够更好地引导公众预期从而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财政政策空间评价
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降费两类政策,不管是哪一类政策,要想顺利实施,前提都是政府债务负担不能过高。如果债务负担过高,政府部门将难以继续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降费,积极财政政策也就难以持续。考虑到债务规模与经济体量息息相关,使用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债务负担较为合理,有鉴于此,本报告主要通过政府债务率的高低,评估财政政策空间的大小。
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债务率不断升高,2020年涨幅尤为明显,到“十三五”末期已经明显超过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2020年中央专门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并且发行了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此外还要求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由此导致政府债务规模大幅升高,即政府债务率的“分子”变大。不仅如此,2020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负,下半年经济增长率与往年相比也明显偏低,由此导致政府债务率的“分母”相对变小。上述两方面因素促使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率在2020年显著升高。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的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政府部门的总债务率涨幅已经达到6.4个百分点,这一涨幅比过去20年间任何一年的涨幅都要大,此前最大涨幅为2009年的5.8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CNBS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政府部门的债务率,如果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考虑在内,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会进一步提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2020年二季度末,中国政府部门总债务率已经达到58.7%,比CNBS的数据高出16.4个百分点。参照BIS的统计口径进行国际对比可知,2016—2017年间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率尚且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018年末和2019年末分别比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7个和1.9个百分点,而2020年一季度末则比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之多。
第二,老龄化等因素还将促使中国政府债务率进一步升高。
导致未来中国政府债务率不断升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疫情冲击和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存在,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继续发力。二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将不断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民生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三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不仅会增加财政养老支出、减少财政收入,进而从“分子端”推高地方政府债务率,而且会降低经济增速,进而从“分母端”推高地方政府债务率。
第三,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偏低和外债占比偏低这两大特征的存在,使得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部门仍然具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
虽然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率正在不断升高,但是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结构与其他经济体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中国政府部门债务风险相对偏低,并且仍然存在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一是,中央政府债务占比相对较低,未来中央政府仍然具有较大的财政政策空间。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央政府债务占比超过90%,相比之下,根据CNBS数据计算得到的2014—2019年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平均仅为42.9%,IMF广义口径下更是只有25.5%。二是,外债占比明显偏低,未来可以适当增加外债以拓宽财政政策空间。通常而言,一国政府对外债的把控能力要弱于对内债的把控能力,因为外债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而且国外债权人通常会在债务国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收缩借贷规模或者提前收回债务,这对债务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爆发欧债危机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政府债务中外债占比较高,希腊和葡萄牙政府债务中外债占比更是高达75%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府债务中外债所占比重在2019年末仅为3.5%,这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风险,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且也为财政政策预留了空间。
三、结语
本报告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双发力,使得货币空间和财政政策的空间都有所收窄。不过,2020年多个经济体大幅降息,从而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实际可操作空间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有所增加。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债务占比偏低和外债占比偏低这两大特征的存在,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部门仍然具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从而拓宽了中国财政政策的实际可操作空间。
为了更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尽可能地预留宝贵的政策空间以备不时之需,“十四五”期间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在严格监管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的同时,适当增加中央政府债务和外债规模,拓宽财政政策空间,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从而更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第二,建议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力度,对于降准而言其主要方向是降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于降息而言则要考虑适当加大单次降息的幅度,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引导信贷市场利率下行以降低融资成本,而且可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从而提高总体调控效果。第三,要更加注重疏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尤其是扫清阻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提高政策传导效率,这样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决策部门尽可能地预留政策空间。
(作者:陈小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编审;陈彦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核心成员)
注: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陈彦斌教授团队撰写的《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21》之分报告五《政策空间评价》的部分核心内容,完整版本的报告即将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21》在持续5年的报告基础上,在“大宏观”和“三策合一”视角下,结合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从“政策目标设定的合理性”、“政策整体效果”、“政策力度”、“政策传导效率”、“政策空间”、 “预期管理”、“政策协调性”七大维度对中国宏观政策进行系统评价。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基础研究,该报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不仅有助于倡导问题导向的宏观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发现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有待改进之处,从而更好地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等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