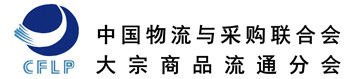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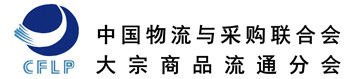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2023-06-21 来源:
编者按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全球储备资产规模持续攀升,储备资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风险持续发酵,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受到青睐。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持黄金储备228吨,较2013年的历史第二高(171吨)高出34%。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持有国。2021年年末,我国储备资产规模为3.4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储备资产份额的22.4%。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保持充裕的储备资产规模、形成合理的储备资产结构、打造健康的储备资产积累方式,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实现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系统研究了全球储备资产结构的历史趋势和形成机制,对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储备资产管理机制有一定指导作用。
《全球储备资产:历史趋势、形成机制和中国启示》
作者:
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熊启跃(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赵雪情(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来源:
《国际金融研究》2023年第4期
《全球储备资产:历史趋势、形成机制和中国启示基于100多个经济体的储备资产微观数据,本文对全球储备资产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全球储备资产规模不断攀升;储备资产持有者集中度稳中趋降,黄金与非传统货币计价资产份额不断上升;“中心”和“外围”国家储备资产结构存在明显差异,金融账户对储备资产形成的贡献度不断提升。浮动汇率制度、货币国际化无法替代储备资产的功能,不应过分关注储备资产的短期账面收益,而要全面考虑其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逐步探寻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储备资产管理长效机制。
01
全球储备资产结构演进
(一)黄金储备:份额大幅下降,21世纪以来触底反弹
在金本位体系下,黄金为主要储备资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全球储备资产规模增速平稳,黄金在储备资产中份额呈下降趋势。1950-1969年,全球储备资产由476.5亿美元升至772.5亿美元,黄金份额由68.5%降至49.0%。牙买加体系黄金非货币化原则的推出,加快了黄金储备份额的下降。2008年年末,全球储备资产中黄金储备的份额已降至6.3%。21世纪以来,储备资产管理者增持黄金储备的意愿有所提高。一方面,1999年,欧洲国家央行签署中央银行黄金协议,对支撑金价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黄金价格与债券实际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对美元外汇储备风险具有较好对冲效果,成为储备资产管理者进行资产组合管理的重要选项。另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使部分国家逐步减持美元储备,增持黄金,例如俄罗斯、委内瑞拉等。2021年年末,全球黄金储备规模为13822亿美元,约占储备资产总规模的9%,较历史低点6%有所提升。
(二)外汇储备:美元有价证券占主导地位,非传统货币份额不断提升
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能够反映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体变化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超过60%。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外汇储备份额持续攀升,并在2000年前后达到峰值。21世纪以来,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日趋多元化,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为代表的传统国际货币份额趋降,而以人民币、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为代表的非传统货币外汇储备占比不断提升。2000-2021年,美元外汇储备份额由78.4%降至58.8%;而非传统货币外汇储备占比则由不足2%升至10.2%。非传统货币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主要储备货币利率水平长期处于低位、电子化技术发展显著降低非传统货币资产交易成本等。
以债券为代表的有价证券是全球外汇储备的主要资产构成。2021年年末,有价证券占主要国家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的85.2%。2008年金融危机前,外国商业银行存款是外汇储备资产重要的配置选项。200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中银行存款占比达到19.6%。2008年金融危机对国际大型银行的信用产生冲击,储备管理者持续缩减商业银行存款。2010年,商业银行存款比例降至7.4%。近年来,外汇储备中金融机构存款份额有所回升,2021年年末已升至15.8%。其中,主权和超主权机构存款替代商业银行存款,成为储备资产管理者更青睐的投资标的。2021年年末,央行及超主权机构存款占主要国家外汇储备比例的13%,较2006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
(三)持有者:集中度变化趋于平稳,“中心-外围”国家存在明显差异
1. 全球储备资产集中度变化趋于平稳
1990-2010年,全球储备资产规模快速攀升,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集中度均呈大幅提高态势。前十大黄金和外汇储备持有者份额分别由1990年的59.7%、57.5%升至2010年末的69.5%、67.4%。2010 年以来,随着全球储备资产增速的放缓,黄金和外汇储备集中度变化趋于平稳。2021年年末,前十大黄金和外汇储备持有者份额分别为69%和65.9%,基本与2010年相当;而最大、前三大和前五大持有者份额均呈下降趋势。
2.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持有份额大幅上升
1990-2008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全球储备资产份额由19.6%升至62.2%。其中,持有全球外汇储备份额由20.9%升至65.2%;持有全球黄金储备份额由13.7%升至16.8%。驱动发展中国家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提高抵御外部冲击 (特别是短期资本急停)的能力;调节汇率,形成更有利的出口条件;降低主权风险和外部融资成本等。新兴市场储备资产规模上升主要由外汇储备,特别是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增长推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新兴经济体逐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贸易逆差程度有所下降等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持有的储备资产份额有所下降,2021年年末降至54.5%。其中,外汇储备份额由65.2%降至56.1%,黄金储备份额由16.8%升至38.2%。
3. “中心-外围”国家储备规模和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中心”国家持有的储备资产规模整体较低,且以黄金储备为主,主要为了保持货币信用。2021年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对外资产总和达1008914亿美元,而储备资产规模为35180 亿美元,占比仅为3.5%。其中,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资产占比分别为1.2%和1.8%。美国和欧元区的储备资产规模分别仅占对外资产的2%和3.1%。作为全球主要货币发行国,美国和欧元区的储备资产均以黄金主导,黄金储备占比分别达到了65%和54.8%。“外围”国家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较高,且外汇储备占主导地位。就“外围”国家和地区而言,储备资产对经济发展、金融稳定乃至地缘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年末,代表性“外围”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 575511 亿美元,储备资产107409亿美元,占比为18.7%。在代表性“外围”国家和地区对外资产中,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占比分别为 16.9% 和1%。如果剔除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准“中心”国家,代表性“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储备资产占比将提升至23%。从全球范围看,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摩洛哥、捷克、波兰等。
(四)货币互换机制的储备替代作用逐渐凸显
2007年,为缓解美元流动性冲击产生的不利影响,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和瑞士国民银行签订临时有限额度互换协议;随后,美联储与14家中央银行签订了更大规模双边互换协议,这些协议全部于2010年到期。2013年10月,美联储与5个盟友国家央行签订永久无上限常备货币互换协议,与9个国家央行签订临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新冠疫情期间,常备互换机制进一步优化,资金成本下降,融资期限拉长,对提振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冲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年7月末,美联储共与11个国家开展1172笔双边货币互换交易。与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丹麦国家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分别开展了607、330、55、10 和 91 笔交易,规模分别达 7921.7、6538.3、920.9、796.5 和 535.1 亿美元。除美国外,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央行也广泛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的推出对储备资产产生了替代效应,是全球储备资产规模下降的重要推动因素。
总的来看,全球储备资产结构变化与各国经济实力变化、全球贸易格局调整、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地缘政治格局愈发复杂的背景下,主权货币充当全球公共品的矛盾更加凸显,全球黄金储备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世界将迎来更加多元化的货币体系,美元和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将继续下降,而人民币的储备资产计价货币地位有望持续提升。随着全球货币互换工具的普及、规模的扩大,其对储备资产的替代效应也将进一步体现,货币互换额度较大国家和地区的储备资产规模将呈稳中趋降态势。
02
全球储备资产形成机制
储备资产的积累主要源于国际收支顺差,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经常账户顺差模式。即通过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初次及二次分配顺差的方式积累。二是金融账户顺差模式。通过FDI、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以及金融衍生品资金的净流入积累。三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模式。1990—2021年,全球储备资产迎来快速增长期,规模由11431亿美元增至153244亿美元,增长12倍多。20多年来,全球储备资产的积累方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亚洲金融危机前,多数储备资产增长较快地区遵循金融账户顺差模式
1990-1996年,全球储备资产规模增长前十地区的外汇储备提高4249亿美元,其中,经常账户累计流入4861亿美元,金融账户累计流出1104亿美元。日本储备资产增幅明显,主要依靠商品贸易和初次收入形成的经常账户顺差,其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则呈现大幅逆差。新加坡也呈现经常账户顺差模式,其顺差主要源自服务贸易,而大量的证券对外投资形成了金融账户的净流出特征。
中国呈“双顺差”模式,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流入是储备资产积累的主要途径。除上述国家外,绝大多数储备资产增长较快地区遵循金融账户顺差模式,例如,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其国际收支主要特征是经常账户逆差(主要由商品贸易逆差和初次收入逆差形成) 和金融账户顺差 (主要由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等短期资本形成)。依靠证券投资和组合投资形成的储备,具有较强的套利特征,需要支付利息和股息成本,受外部市场环境冲击较为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通过“金融账户”模式积累储备资产的泰国、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在危机中遭受较大损失。
(二)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常账户顺差对储备资产形成发挥主导性作用
亚洲金融危机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认识到,金融账户模式,特别是以短期资本“借”来的储备资产并不安全,这些国家积极转变储备资产的积累方式。1997-2013年,主要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增长76362亿美元,其中,经常账户流入76127亿美元,金融账户流入3640亿美元。中国依然呈“双顺差”模式,但主要由商品贸易推动形成的经常账户顺差超过主要由FDI带来的金融账户顺差,“双顺差”中更加依赖经常账户。这一时期,日本、沙特、瑞士、俄罗斯、中国香港和韩国呈经常账户顺差模式,而巴西和印度依然遵循金融账户顺差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依靠“双顺差”和“经常账户”模式的国家在外部冲击下,呈现出更强韧性,而依靠金融账户顺差的部分东欧国家则受到明显冲击。
(三)2014年以来,金融账户对储备资产的影响效果有所增强
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对全球储备资产积累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2014-2021年,主要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增长19108亿美元,其中,经常账户累计流出5160亿美元,金融账户累计流入18540亿美元。这一阶段,储备资产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瑞士,其遵循“双顺差”模式;印度储备资产增幅位居第二,其主要依赖金融账户顺差模式;中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仍遵循经常账户顺差模式;而巴西、美国则主要遵循金融账户顺差模式。
03
我国储备资产演进特征及功能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备资产完成了由接近枯竭到跻身全球第一的蜕变过程。2022年6月,我国储备资产规模为3.21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3.07万亿美元,占储备资产的95.6%;黄金储备1138.23亿美元,占储备资产的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持有量分别占储备资产的0.3%和1.6%。我国外汇储备主要由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外币资产构成。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公开资料显示,美元资产占我国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79%下降至2016年的58%,非美元资产占比从21%上升至42%。我国外汇储备主要为证券资产,货币存款持有量极少。截至2022年5月末,在我国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3.1万亿美元,占比高达99.9%。纵观历史的发展演变,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环境,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储备资产所发挥的功能。
(一)关注持有储备资产的净收益,充分认识其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作用
随着储备资产规模的积累,部分国家和地区已形成超额储备。对这些国家而言,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往往呈现净资产特征,但由于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低于吸引外资支付的股息或利息成本,导致净收益为负,经常账户初次收入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这是持有高额储备资产带来的最主要微观成本。全球承受较高储备资产微观成本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新加坡等。一方面,投资负收益带来的成本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更为审慎的对外资产负债配置策略。具体表现为,资产端强化资本管制,限制私人部门资金外流,强调国内储蓄积累,储备资产出于安全性和流动性考量,主要配置低风险储备货币有价证券;负债端重视长期稳定FDI的引入,但对短期外债强化监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能力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此外,储备资产积累会造成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总量的失控,通过采取恰当政策能够有效进行冲销。当前,应充分认识储备资产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作用。
1. 储备资产积累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拉动作用
经常账户顺差和吸引FDI的储备资产积累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前者有利于推动和巩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支撑国内制造业发展,带动产出和就业,无须承担利息和股息,也不会受到外部债权人(股东)抽逃资金产生的负面冲击。经常账户顺差会通过净出口推动
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助于支撑国内储蓄率,推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FDI是长期稳定资金,有利于促进资本形成,拉动投资增长;同时,通过引入先进管理技术,能够产生“鲶鱼效应”,对促进供应链升级、拉动就业作用明显。历史上,多个经济体都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FDI引入、储备资产积累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1990—2007年的储备快速积累时期,新加坡净出口约占GDP的19%,中国、韩国、泰国“净出口+FDI”对 GDP 贡献度分别为 6.4%、2.3% 和 6.4%。特别是中国,疫情期间“净出口+FDI”对GDP增长贡献度平均近25%。总的来看,经常账户顺差、吸引FDI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此积累的储备资产带来的宏观收益显著大于微观成本。
2. 充足的储备资产对维护金融稳定意义重大
一是在国际流动性不足的关键时期,储备资产可为本国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而储备资产的匮乏,往往导致危机恶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解决日资企业外币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日本曾动用储备资产向国际协力银行(JBIC)拆借,满足日资企业的海外融资需求。2022年,斯里兰卡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其不足5000万美元的外汇储备无法偿付7800万美元到期债务利息 (存量债务510亿美元)。由于无法偿付食品、药品和燃料在内的进口商品,斯里兰卡通胀率高企,并停止向普通民众出售燃油,危机不断扩散。
二是储备资产被用于机构注资与重组,能够有效夯实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银行动用储备资产出资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注资。近年来,在部分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中央汇金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储备资产还被用于向政策性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注资,对夯实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提升金融体系稳健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储备资产可用于建立稳定基金,缓解市场动荡带来的不利冲击。为缓解原油出口收入波动对财政体系带来的冲击,俄罗斯、挪威、科威特、委内瑞拉等原油出口国,通过储备资产建立“原油稳定基金”。当原油出口收入较高时,部分预算外盈余收入将被转移到原油稳定基金;而当原油收入较低时,稳定基金将弥补财政收入预算缺口。“原油稳定基金”对挪威等国家增强财政体系的稳健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稳定外汇市场,保持外币流动性,英、美、法、日、韩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有通过储备资产设立“外汇平准基金”的实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香港运用外汇储备成立平准基金,对抵御国际游资做空港币、港股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美国外汇稳定基金 (ESF) 资金来源全部为SDR,而资产端主要配置欧元和日元低风险资产、美国政府债券和SDR。2022年5月末,美国ESF资产规模达到2221亿美元。
四是储备资产能够提高本币信誉,为政府及企业国际融资提供保证和背书。对于货币体系“外围”国家而言,储备资产的增多能够显著提高外部评级,降低对外融资信用溢价,减少融资成本。
(二)浮动汇率制度无法取代储备资产功能
1. 全球步入浮动汇率时代,货币锚发生根本性变化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全球货币与黄金脱钩,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根据IMF统计,约33%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约20%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硬盯住的固定汇率制度,47%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软盯住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一转变下,各国特别是非主要货币发行国持有外汇储备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升。一是汇率盯住的锚不再是黄金。除了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其他汇率制度在不同程度上盯住某种货币、某几种货币或者通胀等指标,均需要储备资产予以调节和保障。二是汇率锚受制于美国等主要货币发行国,面临更大的政策溢出效应,储备资产成为抵御冲击的重要屏障。三是汇率波动幅度增大。长期汇率取决于基本面因素。但是,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跨境资本流动增加,短期汇率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可能出现超调风险,引发市场失序、定价混乱,严重危害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因此,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汇率可以无限制自由浮动,某种程度上出口等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决定了汇率浮动边界。例如,2013年我国企业平均出口利润率不足3%,近年随着竞争力提升,利润率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中小企业出口利润仍较为微薄,一旦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将遭受巨大损失。
2. 浮动汇率制并未消除货币危机,充足的储备资产是缓释汇率风险的重要保障
历史经验显示,即使许多国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仍陷入货币危机乃至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亚洲金融危机前,印尼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危机后转为自由浮动汇率制,但在2008年、2013年、2018年仍难逃金融风暴;土耳其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但2018年爆发货币危机,里拉兑美元贬值超过78%。
储备资产是调节汇率波动、防范货币危机的重要屏障。一方面,央行可以动用储备资产,直接参与市场交易,配合货币政策,调节本外币供求,释放稳定信号。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储备资产仍为影响市场预期与汇率水平的重要因素。例如,2015年“8·11”汇改与美联储加息背景下,我国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甚至出现短期超调现象。我国加大外汇干预与资本管理,在2015年末至2016年期间消耗了近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满足对外偿付的基本保证,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巩固投资者信心,降低投机攻击、资本外流以及外部冲击的传染共振效应,进而防范潜在的货币危机。
当国际资本与本国政府博弈,央行储备深度成为抵御货币投机、对赌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国家外储规模较低,成为国际资本狙击的对象。中国香港依托自身与内地的庞大储备,有效抵御国际资本狙击,较为平稳地渡过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吸取经验教训,增加储备资产积累,用以防范金融危机。例如,韩国经常项目赤字与过度举借外债,外汇储备曾一度枯竭,1998年危机时期甚至依赖民众“献金救国”。危机后,韩国实行出口拉动战略,重点加强外汇储备积累,用于降低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截至2021年年末,韩国外汇储备规模达4375亿美元,较1997年增长逾20倍。
(三)储备资产是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基石
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储备资产。相反,充足的储备资产对于货币国际化进程至关重要。即使在本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后,发行国储备配置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仍需保有相当规模的储备资产。
1. 在起步阶段,充足的储备资产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意味着超主权信用,充足的黄金储备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英国曾是全球最大黄金储备国,为英镑国际使用奠定了信用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成为美元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本保障。随着国际货币格局步入牙买加体系与浮动汇率时代,充足的储备资产可以有效降低汇率波动,维护金融环境稳定,调节国际收支,进而夯实货币的国际信誉,对于货币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 货币国际化以贸易顺差为起点,伴随着国家实力崛起与储备资产增长
理论与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大国崛起紧密相连。随着货币发行国生产率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本币以贸易顺差为起点,开启国际化进程。19世纪中后期,美国快速工业化,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贸易规模一度占全球三分之一。20世纪40年代,美元正式确立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美国长期保持进出口顺差,储备资产规模总体呈增长态势。从德国、日本经验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经济快速恢复,德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日本进出口持续保持较大顺差,成为货币国际化的基石,并带动储备资产规模增长。
3. 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有所下降,但是仍保有适度的储备资产,配置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
数据显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均持有较大规模的储备资产。截至2021年年末,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官方储备金额分别为 6999.5 亿美元、2960.9 亿美元、2391.9 亿美元和 14057.5 亿美元。随着本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能够满足国际支付、流动性及安全性需求,发行国将相对减少外币资产持有量,调整配置结构。一方面,储备资产中外汇资产占比与货币国际化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例如,美国、欧元区 (德国)、英国外汇资产持有份额显著低于日本。另一方面,储备资产构成也受到自身国情、资产收益、安全性考量以及历史因素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德国积累了大量黄金。日本储备资产中91%为外汇资产,其中包含大量美元计价资产。截至2021年年末,日本持有美债规模达1.3万亿美元,成为美债第一大外国投资国。这不仅有助于稳定汇率与外贸,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地缘政治考量。此外,货币互换成为外汇储备的补充内容。近年来,美国等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主导建立了货币互换体系,以应对“美元荒”局面。随着2008年危机以来货币互换工具的广泛使用,其也成为核心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或有选项。
4. 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初级水平,我国对外经贸投资仍高度依赖美元等主要外币
近年来,全球货币体系日趋多元化,但在国际支付、金融交易以及外汇储备中美元居绝对主导地位,人民币使用份额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人民币收付金额为5.8万亿元,约占进出口总额的15%,某种程度上约85%的进出口依赖美元等外币结算;2022年前5个月,在我国银行业代客涉外收付款中,美元占比为53.5%,较人民币高出12个百分点;美元在我国外汇交易市场、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银行业对外金融负债中占比分别高达96%、67%和36%。自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近13年,我国对外经贸投资结算币种结构缓慢变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短期内难以改变。尽管我国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订一系列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22年年末总金额近3.7万亿元,但与美国的货币合作依然收效甚微,难以有效补充潜在美元需求。因此,我国依然需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储备资产特别是美元储备,以满足基本的国际收支需求与流动性缓冲。
(四)储备资产正沦为强化金融制裁的工具
1. 地缘政治因素对储备资产配置的影响不断增强
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影响一国外汇储备配置策略的重要因素。Eichengreen et al.(2017)研究表明,军事联盟会促进外汇储备中盟友货币份额的增加,能够平均使盟友货币份额提升30个百分点。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部分国家外汇储备调整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愈发明显。例如,自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俄罗斯大幅减持美元外汇储备。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沙特阿拉伯,其外汇储备的构成中美元所占的份额较高。
2. 储备资产已成为美国开展金融制裁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美国不断利用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对他国储备资产进行制裁。2019年,美国发布总统行政令,宣布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全部资产。2022年2月,美国签发总统行政令,宣布将阿富汗中央银行近70亿美元储备资产冻结,并考虑将这些资产罚没用于赔偿“9·11”遇难者家属。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中央银行、财政部和主权财富基金纳入非SDN菜单式制裁清单 (NSMBS List),其核心条款包括对俄罗斯美元储备资产冻结。此外,美国还针对与俄罗斯开展黄金储备交易的主体实施“二级制裁”(熊启跃和赵雪情,2022)。
3. 地缘政治变局下我国储备资产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2021年年末,我国储备资产规模为3426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资产的36.8%,是我国对外资产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我国储备资产中,外汇储备为32502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131亿美元。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但对美元和欧元等主要储备货币依赖度依然较高。随着大国博弈加剧,我国需要更加重视储备资产安全。考虑到储备资产总量需求短期内难以压减,未来我国储备资产管理面临的核心任务在于尽快调整资产结构与布局,进一步提升储备资产分散化、多元化水平。
04
启示
作为全球最大的储备资产持有国,应清醒地认识到,储备资产的形成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近几十年来,大规模的储备资产是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当前,应审时度势,客观分析局势变化,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进一步科学优化储备资产管理,逐步探寻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储备资产管理机制。
(一)保持储备资产稳健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储备资产的形成与积累,是长期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政策发挥效力的结果,健康的“双顺差”储备形成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就业拉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对外资产结构的形成是基于金融稳定、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多重因素考量的结果,应全面评估综合收益,而不能仅仅关注账面财务回报。“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维持和巩固健康的储备资产增长方式,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持经常账户顺差和FDI流入的储备资产形成方式,适度控制通过短期外债形成的储备资产。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特别是货物贸易顺差,加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产品附加值,巩固制造业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降低集中度风险。继续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放松股权比例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加大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适度加大长期股权和债券投资的外资吸引力度,不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对外直接投资质效,提高我国相关产能延伸市场投资效率,防止无序产能转移可能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发挥储备资产作用,支持对外援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投资粮食、原油、矿产等关系国家产业链安全的重要领域。
(二)发挥储备资产风险屏障功能,维护我国金融稳定
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我国仍处于“外围”国家的地位,外币流动性的补充渠道相对有限。储备资产的金融稳定效应是“无价之宝”,安全性和流动性仍是我国持有充足储备资产的首要考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国际经贸投资中外币,尤其是美元的使用程度较高,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率较低,对汇率变动高度敏感。近年来,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呈“喇叭形”,波动幅度显著增大。从存量来看,2021年年末我国对外负债为7.3万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占比达50.5%,较201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从流量来看,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流动规模从20世纪末的约474亿美元扩张至2021年的8541亿美元,过去十年季度净流动的波动率较2000—2010年增大逾1.1倍。短期资本流动对政策与市场极为敏感,可能顺周期出现大进大出的局面。此外,我国私人部门对外资产配置比例较低,对国内增长并未形成一致性预期,存在一定的资本流出动机。2021年年末,我国对外资产中非储备资产/GDP比例为33.8%(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高达150%、255%和193%),大量私人部门财富聚集在国内,集中配置于银行存款和理财、资本市场有价证券。2019年年末,我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达325万亿元。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居民主体预期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不排除大量私人部门财富通过非官方渠道外流。我国需要保持充足的储备资产,平缓短期资本大进大出,作为防范外资流出、本国资本外逃的安全屏障。
(三)保持充足的储备资产规模,维持汇率稳定
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提高,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愈发明显。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汇率无限制地自由浮动,其浮动边界应受到出口导向性企业盈利空间、经济主体资本流出压力等因素制约,保持充足储备资产是实现汇率“有管理”浮动,降低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负面冲击的基石。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加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快速收紧,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发力阶段,需更好地发挥储备资产稳定汇率、引导预期的重要作用。我国应完善汇率超调预警机制,优化储备资产在汇率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平衡好外汇储备干预与外汇储备充足性的关系,充分发挥储备资产的预期引导功能,提高外汇储备直接市场干预的效率。加强宏观调控政策、资本管制政策、市场沟通机制的协同,充分发挥政策合力。
(四)黄金储备:份额大幅下降,21世纪以来触底反弹
面对地缘政治变局,我国需多措并举,调整储备资产结构,建立区域缓冲屏障。
1. 优化储备资产结构,保障储备资产安全
一是降低外汇储备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适当丰富外汇储备形式,减少有价证券的持有比例,增持“友好”国家央行或商业银行存款。二是根据市场走势,建议适度增加黄金储备。近20年来,全球储备资产增配黄金的趋势较为明显,全球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已升至10%,而我国目前黄金储备份额不足储备资产的4%。推进境内黄金交易所发展,将黄金储备移至境内或“友好”国家托管。三是运用外汇储备购置能源、粮食、关键资源和战略性物资,丰富储备资产结构。以外汇储备设立专门基金,参与中资企业在战略资源供给国的资源产业投资。
2. 增进区域货币合作,建立金融安全屏障
我国应继续巩固与东盟、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等区域经贸合作,重点推动将货币金融合作纳入经贸合作框架。加强区域内本币使用与系统对接,探索区域内净额轧差结算,改革推动清迈协议、金砖国家应急储备等机制发挥实效,构筑“免疫制裁”、降低外汇储备需求的区域缓冲地带。同时,对于经贸联系密切,尤其是战略资源供给国,深化双边本币合作,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沟通,拓展本币结算协议,推动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互设,扩大金融市场准入与系统对接,丰富本币计价风险管理工具。升级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优化使用额度、频率、范围,进一步打通企业—银行—央行申请使用路径,探索建立永久性常备互换机制。
3. 藏汇于民,探索打造境内外汇自平衡体系
为了降低外汇储备需求压力,改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有效缓释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建议充分动员境内私人部门外汇资金,通过债券融资、资产管理等方式,有效对接境内外汇持有方与使用方,推动形成境内外币资产市场与投融资的闭环网络。
4. 加强储备资产精细化管理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呈净资产特征。2021年年末,我国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规模比必须支付利息(股息)的负债规模多2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受资产负债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投资净收益率长期为负,整体收益亟待提升。在满足储备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功能的基础上,我国要加强外汇储备分级管理,实施差异化风险考核和投资回报要求。允许具有较高资质的商业性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储备资产管理。允许储备资产适度提高风险偏好,提高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