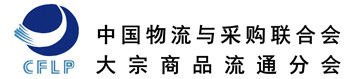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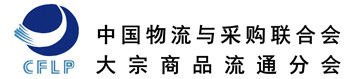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2024-02-06 来源:
作者:张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原文出处:张晓晶 主编、张明 副主编:《金融学前沿报告20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引言 世界经济几千年的发展史中,经济增长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不平衡的。在古代,海洋、山脉、沙漠、冰川等地理因素阻碍了国家之间的交流,一座山脉分割下两个国家可能千年没有往来,每个“与世隔绝”的经济体独自繁荣自己的经济和文明。伴随着人类的探索和科技的进步,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开始逐渐交织在一起,相互关联、互相影响。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通过定量分析不同国家的人口、经济规模和生产率的变化提出,过去一千年中各国的经济表现可以由三个互相关联的活动所解释:对人烟稀少、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方的占领和殖民、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诚然,麦迪逊精简概括了分割的世界如何共同走向现代文明中的关键因素,但他更多地是基于历史的视角,缺少经济学理论的归纳。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Acemoglu和Zilibotti(1997)提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分割的经济体只能投资于有限的项目,无法通过多元化分散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从而在历史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下出现了发展较好的“幸运”国家和发展不好的“不幸”国家,各国经济表现的参差不齐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消除或缓解各国经济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Obstfeld(1994)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即经济(金融)全球化。各国可以投资于全球的项目,多元化降低了单一异质性风险的冲击,全球国家都可以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稳态的福利收益。根据Van Wincoop(1999)的估算,全球化带来OECD国家可贸易品消费增长从1.1%到3.5%(50年区间)。恰如所料,Bordo和Helbling(2011)考察了120个国家1880-2008年的历史产出数据,发现全球化时代(1986-2008)各国的产出相关性最强,各国均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了福利改进。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开始下降,现实表现出明显与全球化理论相悖的事实。虽然有些学者将原因归咎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分化、制造业份额的下滑、外生冲击下的供应链阻断等,但依然不可驳斥的是我们尚未厘清经济周期跨国传导的机制。典型举例,如果按照新古典的假说,全球化之后会观察到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而Lucas(1990)观察到,资本反而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聚集。这说明,一方面,基于高度抽象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型,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需要可以“落地”的机制讨论和微观数据验证,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有关国家之间的联系,更是一个涉及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交织混杂的领域,传导机制的讨论不能“悬浮在半空中”,需要一个简明理论对机制进行概括总结。 当下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关键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如何更好地应对外部事件的冲击,在时代翻涌中把握好中国经济远航的舵盘,需要我们对经济周期的跨国传导有准确的理解和感知。本文将详细地对经济周期跨国传导的机制进行文献评述。
以下为正文内容: 1 要素禀赋与经济周期 在经济周期的传导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各地的要素禀赋。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Aghion and Durlauf,2005)中看,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一方面决定了是否有可能走相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禀赋的互补性决定了各国能否在相互交流中获得整体福利改进。依据要素禀赋流动性的差异,地理和气候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基础和长期,它们是完全不能流动的禀赋因子,例如于世界各国而言,河流冲击下的三角洲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历史和文化因素作为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表达,它们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改变的,而是需要很大的外生冲击或长达几十年的逐渐演变,例如佛教的起源地印度,现在大部分民众信仰印度教;以矿产、油气等自然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禀赋,在地理是无法移动的,但可以通过出售采矿权、国际贸易等形式进行流动;相对而言,人口和技术的流动更加成本低廉,但现实中常常会施加政策约束,增加人口和技术流动的成本;资本在当代社会是流动成本最低的要素禀赋,但受资本管制的直接影响。本小节将从这四个方面依次展开。 (1)地理和气候 在古代社会,每个国家主要与地理上接壤或交通便利的国家进行交流,距离越远则国家之间的交流就越弱。现代社会依然如此,在贸易和投资的决定因素的讨论中,距离因素始终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Rose,2000)。地理因素虽然最为直觉,但也是非常难以论证的。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强调地形复杂崎岖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是通过排除其他替代性假说的方法进行论证,例如通过例证和引用生物学的研究驳斥国家之间的差异是人种(遗传基因)决定的。与排除替代性假说的方法不同,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23)利用一个动态空间模型阐述了地理因素在国家形成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将世界分割为六万多个六边形土地,每个六边形代表一个国家,相邻国家有概率发生战争,土地生产力高的一方获胜并占领失败方的土地。地理因素在模型中表示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如果地形越崎岖,越不可能出现战争和战后的占领行为。在多次进行500期的模型模拟中,结果稳健的出现了统一的中国和分裂的欧洲,说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地理因素于经济发展的“原罪论”是很多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观点,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23)的研究在支持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地理因素是否带来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是关键,在非洲和美洲的模拟中发现,在土地生产力受到其他因素(如气候)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地理因素的解释力大大下降。 与地理因素相似,气候因素的论证也面临同样难题,但好在气候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变化,数据支撑下的论证更加具有说服力。Zhang等(2007)整合了多个研究数据集,将时间回溯至1400年探讨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时间维度上战争的频率和人口变化的波动遵循温度变化的周期,在空间维度上寒冷气候期间人口稠密地区(欧洲和中国)的战争爆发数量和人口下降程度更高,从而得出结论:气候变化是战争爆发和人口数量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诚然,丰富的数据集使这份研究非常的引人注目,但在分析方法是依然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Waldinger(2022)将重心放在欧洲大陆印证了上述观点,两篇研究的气温数据相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本篇文章采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控制了地形、离海边距离、适宜种植农作物的程度、宗教等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地区人口变化的变量,依然发现气候变化对城市发展(人口)的影响。 (2)自然资源 地理因素、气候变化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完全无法流动。人类如果想要避免地形崎岖对经济的影响,就迁移到其他地形平坦的地区进行发展;干旱少雨的内陆不适宜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就迁移到其他适合农作物耕种的地区进行生活。正是因为这些地理、气候这些因素是无法流动的,所在国家只能默默接受,所以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传导的讨论中,这些因素常常予以忽视,而不会极端地提出发动战争的“政策建议”。毕竟还有一些资源禀赋是可以流动的,比如矿产、石油、煤炭,这些生产要素依然非常重要。 关于资源禀赋最经典的讨论就是Sachs和Warner(2001)提出的资源诅咒(Natural Resources Curse)。他们观察到很多贫穷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比资源匮乏的国家增长的更慢,而地理和气候因素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他们猜测可能是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沉醉于资源出口的获益,忽视了工业制成品生产和贸易。Van der Ploeg(2011)认为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未来过分乐观,沉醉于当期享受,并缺少对寻租行为的制度性规范。如果这些国家能够看得更加长远,进行制度建设和具备生产力的投资,就会转化为资源的祝福。 坦诚来讲,资源诅咒在很多时候是有悖于传统的直觉,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丰富按理说会推动进行的快速增长,为何反而会导致经济的落后呢。其中一个潜在的解释就是,自然资源丰富可能是一个内生因素。很多经济史的学者论证出煤炭对于工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煤炭资源的发现可能是内生的。Fernihough和O’Rourke(2021)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古代煤矿的位置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当地寻找煤矿的努力,或者说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副产品。直接来讲,煤炭资源虽然历史上就在当地了,但是能不能发现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强相关的内生性行为。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观察到遭遇资源诅咒的国家大多拥有被殖民的历史,这些国家的资源是由其他国家的殖民者发现,资源诅咒更多地是“历史诅咒”。 资源诅咒的讨论仍在继续,可以确定的是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会驱动各国经济周期的联动,尤其是拥有相同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基于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Fernández等(2018)在小型开放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资源禀赋部门验证了这一机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对于自然禀赋国家产生直接的收入冲击,影响国内需求和实际汇率,进而对各个宏观变量产生冲击和影响。与之类似,Drechsel和Tenreyro(2018)基于两部门开放经济的RBC模型,最终商品的生产需要大宗商品、资本和劳动三者的投入,也发现大宗商品价格驱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 (3)历史文化 与前述的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历史文化因素是可以随时间而逐渐变化,并可以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另外一个国家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禀赋,大概率是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但如果仅仅是想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则可以通过宏观政策达到文化的改造。 历史文化因素中,于经济周期有最强解释力的无疑是殖民地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国家的经济联系,还体现在被殖民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Rose,2000)。这种经济联系一方面体现出经济交流所展现出来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殖民地关系背后是两国之间文化联系、相似法律契约制度和人员往来。但Head等(2010)发现殖民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是双方选择的结果,对于殖民国家而言需要寻求更加多元化的贸易网络;对于殖民地而言需要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相较于殖民关系,语言在链接两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上的结果要更加多元。一方面,语言相似程度会促进双方的贸易,投资者也更愿意购买可以用母语进行交流的国家的股票(Grinblatt and Keloharju,2001;Melitz and Toubal,2014)。另一方面,语言背后是历史和价值观(Spolaore and Wacziarg,2015;Desmet et al.,2017),落后地区的人会学习发达地区的语言,期望能够凭借语言优势达成合约,获得更多机会。 信任也是影响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文化因素。Guiso等(2009)使用一个独特的数据可以看到欧洲国家之间双边的信任关系,通过这一详细的数据发现即使控制了两国特征之后,信任依然能够显著提升两国的双边贸易和投资,他们称之为“Cultural Bias”。这一结果非常强并且具有冲击性,在于双边特征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地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4)人口和技术 与上述所有禀赋条件不同,人口和技术禀赋的流动要远远快于文化、资源和地理因素,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传导中,不可忽略的就是人口和技术流动产生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一影响的识别在现实中非常困难,一方面难以排除地理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干扰,人口和技术更倾向于流入地理相近、历史文化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难以排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人口和技术流动会伴随着贸易和资本流动产生的联结而强化。这就使得虽然人口和技术的流动于经济周期的作用非常重要,但罕有文章直接就这一问题开展强有力的研究。 在传统的外生增长模型中,关于技术主要有两个设定:使用技术的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技术投资的回报兼具私人和公共。从而,技术的使用可以提升全世界的生产率水平,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但事与愿违,随后学者们观察到:获取和使用技术是有成本的,甚至成本高到不如自己进行研发;投资技术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回报可能被限制在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进而,一系列技术转移(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模型发现,在空间上,对技术创新的接纳程度高、技术投资的获益高、专利保护力度强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稳态增长水平(Keller,2004)。Liu等(2022)使用USPTO的专利转移数据和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对专利转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中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由35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跨境专利流动“小圈子”的网络特征日益明显。在圈子内的国家之间技术流动迅速且频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强;但是圈子内外的国家之间较少有技术的流动,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弱。他们的发现也是与经典理论模型的结论相悖,在现实的世界中国家存在非常强的异质性,融入全球化的条件是需要本国有足够的专利产出或专利应用市场,否则拥有高精尖技术专利的国家并不会“施舍”技术给完全没有经济收益的国家。 人口流动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高技术移民的积极作用几乎为大家所公认(Peri et al.,2015)。相较于人口流入,人口流失的讨论则存在两种对立的效应:Beine等(2001)提出了一个观点,人口流出对于国家来讲有两个效应:脑力效应(Brain Effect)和流失效应(Drain Effect)。脑力效应是指,由于海外的回报较高,为了未来能够移民海外加大了教育投入,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流失效应是指,人口流出尤其是高教育水平的人才流失。他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流失效应,但建模较为简陋。Agrawal等(2011)利用丰富的数据集控制了专利活动在地理位置和种族空间上的分布,发现人才流失(高技能移民)并不会将来源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消耗殆尽,反而能够通过网络外部性提升移民来源国的经济增长。然而,对于最贫穷的国家而言,过于前沿的技术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无推动作用,因而在这些国家的流失效应要更加明显。 (5)资本 在当今社会,资本是最容易流动的要素禀赋,但是资本的流入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有利的事情,资本的快速涌入、涌入停止、流出和迅速反转都可能会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Forbes and Warnock,2012)。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资本的流动已经不仅仅表现在要素禀赋的变化上,更多地是通过资本流动形成国家之间股权交织的网络,以及资本流动衍生的金融危机等问题,后者于各国家之间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要更大。本节主要从经济增长的模型出发,讨论资本作为重要的要素禀赋在联结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作用,而资本流动交织而成的网络以及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将在后文的章节进行阐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资本要素上的差异会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的差距被显著拉大。因而如何积累资本,并利用资本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方法之一就是资本配置,这里的资本配置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通过储蓄让资本在代际之间分配,第二是资本在不同主体、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关于资本的代际分配,涉及到储蓄率、遗产税、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Feldstein,1974;Kotlikoff and Summers,1981;Dynan et al.,2002),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社会制度安排让微观主体更多地将资本投入到具有生产力的环节和部门,降低预防性储蓄,提升整体的当期资本投入服务于经济增长。关于资本的部门间分配,首先,资本的增长必然会带来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增长,形成“不平衡的增长模式”(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金融在部门间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Bustos等(2020)的研究以巴西采用转基因大豆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外生实验,发现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会导致储蓄增加,这些储蓄并没有在当地进行再投资,而是通过银行网络投资于其他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 积累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利用国外资本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服务。这一论述非常符合直觉,但很多时候过于理想化了。正如本文引言中所提到的,Lucas(1990)观察到资本并不是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反而是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随后,一系列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比如Prasad等(2007)、Berg等(2012)、Gourinchas和Jeanne(2013),这些文章的核心逻辑无过于两个:第一,外国资本是否与本国的生产要素相匹配(如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匹配);第二,本国对于外国资本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并且需要相对的稳定性。对于前者而言,当落后的国家亟需外来资本帮助本国实现工业化的时候,资本流入了自然资源的开发领域,反而会增加对本国经济的掠夺与伤害;对于后者而言,当落后的国家对于资本流入的吸纳是有限的,过多的资本流入抬升了估值,导致收益率下降,反而伴随着后续的资本获益离场,冲击经济稳定。 2 生产网络与经济周期 与要素禀赋的讨论不同,生产网络的讨论中更加关注国家之间的交流、交互作用,从而形成紧密联系、分担风险、共享增长红利的经济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贸易的作用,这一块的文献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并且近些年来贸易领域的文献做的越来越精细化,是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领域。但是,贸易文献于现实世界的背离点在于,现实中不仅存在可贸易品,还存在不可贸易品,这一部分常常无法遵循贸易文献的研究范式进行深入讨论。并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家发现不可贸易品(如金融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传导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以及背后的投资网络在其中作为至关重要的微观主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垂直贸易与供应链网络 在经济周期的跨国传导中,学者关注最多的一个领域就是贸易,贸易也是文献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石,是各国实现全球交流网络的重要环节,但是传统的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有限,反而可能在外部冲击的作用下导致经济周期的分离。典型的,石油冲击对于产油国和石油消费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影响,必然会导致经济周期的背离(Mork et al.,1994)。因而,在实证研究中看到,贸易联系在解释经济周期同步性上并不是一致稳定的表现为正显著(Cerqueira and Martins,2009)。 最初,大家在解释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联动性这种差异性结果的时候,主要关注产业(贸易)结构。逻辑在于,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工业生产和贸易结构非常相似,那么两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会相似,在遭遇全球共同冲击时反应相似,从而各国经济周期也会一致。然而,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种假说(Garcia-Herrero and Ruiz,2008;Ng,2010)。其中一种解释是区分冲击的类型,如果是供给冲击,产业结构相似的两个国家遭遇同等冲击,但如果是需求冲击,产业结构相似的两个国家便面临直接的国际竞争,结果可能是一个国家相关产业的衰落。典型的汽车产业,在需求端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德国、日本、美国的车企开启存量竞争时代,一国在汽车行业收入的提升必然以其他国家收入的减少为代价(Williamson,2001)。 根据Backus等(1992)关于国际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伴随着国家贸易的繁荣各国会依照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而他们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到贸易成本的影响。Kose和Yi(2001)引入了贸易成本到标准的国际经济周期模型之中,得出结论:高的贸易成本会导致低的各国产出相关性。他们认为,伴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各国更加倾向于从事商品生产的某一特定环节,而不是生产整个产品,国际贸易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产品进入加工后再流出(back-and-forth)的贸易模式,这会增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连接,从而表现出相似的经济周期。实证方面想要证实这一观点非常有难度,所以挖掘产业链供应链关系成为检验这一观点的重要手段。 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在实证中的挖掘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使用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来度量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大家最常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数据,根据各国的监管要求,一般超过销售额(成本)10%的客户(供应商)身份将会在年报中进行披露。Barrot和Sauvagnat(2016)发现美国公司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会给他们的客户带来巨大损失,客户的销售额增长会下降2-3%,股权价值下降1%。第二种,需要交易信息和交易对手完整的财务信息。因为对数据的要求很高,所以相关的文章产出较少,但这些额外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强弱,进行更加细致的估计。例如,Alfaro-Ureña等(2022)利用哥斯达黎加的数据提出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会使国内企业业绩出现爆炸式的持续增长,原因是规模更大的需求和更加稳定的供应商关系。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与产业竞争的作用相反,全球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形成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即使单一企业遭受了外部风险冲击,也会沿着产业链供应链传导至上下游的企业,造成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Costinot等(2013)对此进行了建模,但是他们提出技术进步对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国家会造成不同的冲击,因而并不是完全的风险分担,各国经济周期依然存在差异。 (2)贸易壁垒(成本) 既往我们在讨论贸易成本或交易壁垒的时候,常常考虑的是地理成本(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制度成本(两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等是否一致)。而伴随着国际经贸格局的变迁、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大家看到交易壁垒可能体现在多个维度之中。最典型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大家意识到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于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机制路径就是同一产品的多个生产工序、多个中间品生产在不同国家完成,同一个需求冲击影响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国家。例如,Ferrari(2019)从产业的视角进行考量,当面临最终需求冲击的时候,产业链上拥有更多生产步骤(产业链条更长)的行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Meier(2020)假定生产是分多期进行的,如果供应链中断则会延长生产的时间。Lossifov(2014)发现中东欧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在提升,原因在于中东欧的出口商在逐步融入欧洲经济活动的价值链。在识别上,最困难的在于历史和地理因素常常与产业链联系难以分割。Finck和Tillmann(2022)采用三个外生事件:日本大地震、Ever Give阻塞苏伊士运河、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政策,进一步论证了产业链联系在传递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完全独立生产全产业链的所有商品,是可以隔绝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Costinot et al.,2013)。但是供应链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灾害可以摧毁基础设施并且破坏交通运输,税收和关税变化导致供应链的重新调整,生产或运输公认的罢工、恐怖袭击、传染病等抑制了中间产品的流动,可以说想要完全消除供应链中断的危机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提升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微观上,Alfaro-Urena等(2022)发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四年后,企业的雇佣工人数增加2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4-9%。宏观上,Bonadio等(2021)做了一个评估,假定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是一个劳动力供给冲击,如果国家采取供应链国有化,国家将会面临更大的经济衰退。无法做到,也不应出于对供应链传导经济周期的恐惧而减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参与。 (3)跨国企业 跨国公司连接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就是生产力冲击通过跨国企业内部转移至各个国家(Cravino and Levchenko,2017)。在实证的论证时,常常使用跨国企业入驻或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产出、就业的影响来度量这种机制。这种方法的内生性不言而喻,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通常是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潜力大,跨国企业才会选择入驻或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Gong(202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设定,利用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开设子公司的数据,当一家跨国企业A出现技术突破之后,对比其在中国子公司附近的中国企业与没有发生技术突破的跨国企业B在中国子公司附近的中国企业,同时使用美国各州的研发税收抵免政策缓解“经营绩效更好的企业更有钱投入到创新活动之中”的内生问题。当然,这种机制可能过于理性化,Glass和Saggi(2002)就揭示了东道国和跨国公司的博弈,只有当跨国公司转让技术或培训本地员工获得知识技术积累时,东道国才会欢迎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反,东道国可能会有动机阻止跨国企业的投资。 跨国公司影响各国经济增长一个非常直觉的机制就是通过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方面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事实可能与我们预期的不一致(Ramondo et al,2016)。跨国公司整理纵向资源的重要渠道是无形资产的分配和转移,例如销售目的地市场的资源。内部贸易促进跨国经济周期联动缺乏证据支撑虽然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但却是与日益全球化的国际金融连接相一致,各国设立海外子公司的目的可能不再是为了便利贸易和降低交易壁垒,而是出于增加股东价值、避税等综合的考虑(Erel et al.,2012;Gumpert et al.,2016)。 进而,跨国企业在传导各国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因素,股权(金融)联系,开始变得日益重要。Bena等(2022)直接检验了跨国企业股权联系在传导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他们同样采取了一个基于匹配思想的设定,如果一家跨国企业的子公司位于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会通过跨国企业传导至其他国家的子公司的投资和就业,这种机制在非贸易品行业的子公司也是显著的,部分支持内部资本市场在传播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这一点在既往文献中也多有提及,但强调的要点是拥有内部资本市场的公司能够在金融危机和负面经济冲击下保持经营的稳定,从而可以平滑各国异质性冲击的影响(Matvos and Seru,2014;Santioni et al.,2020)。 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在规模上的累积,也会产生宏观影响,使得我们低估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联系。Coppola等(2021)便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跨国企业常常通过在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来为母公司融资或者代理投资行为,如果穿透持有人的股权结构,美国持有中国企业的股权超过7000亿美元,而官方统计仅有1540亿美元。国际资本市场的存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个发达国家普遍走入了负利率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更愿意在国际市场而不是本国市场获得资金,不仅体现在股权融资上,还包括债券融资和银行信贷。在跨国企业的作用下,不同国家的融资壁垒和资本管制被打破,税收筹划使得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更加复杂,流动性管理和汇率风险管理将各国的金融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变得空前紧密。Kleinert等(2015)将其形象地归纳为少数引领多数(the few leading the many),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很大程度受上两国之间少数(大型)跨国企业的影响。 3 共同冲击的影响与经济周期 要素禀赋和生产网络决定了日常时期各国的经济周期,但各国的经济周期的同步与背离,离不开全球共同冲击的影响。Bordo和Helbling(2011)在总结历史上经济周期传导的经验时就指出,从长周期来看,全球各国经济呈现一定的同步性,是因为要共同应对外生冲击的挑战。当然,于单个国家而言,外生冲击可能并不是一定是全球的共同冲击,大国的一举一动可能会深刻影响小国(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更具挑战的是,在信息技术和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个毫无关联的国家、行业的信息,都可能通过模仿效应冲击本国的经济周期。因而,共同冲击在当今时代有更加广泛的含义。 (1)灾难冲击 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也必然会成为驱动两国经济周期同步的一个共同因子。例如,针对于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的研究就发现,海啸造成了沿岸各国经济产出的下滑和巨大的人员伤亡(Athukorala and Resosudarmo,2005)。然而,虽然自然灾害普遍认为是外生的,但是灾害冲击的大小普遍认为是与国家的收入水平、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Kahn,2005;Toya and Skidmore,2007)。尤其是到21世纪,学者们发现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好像并没有那么强。典型的,Cavallo等(2013)发现只有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才会对产出造成影响,而一旦控制了灾难后的政治革命,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消除。这里就出现了实证证据与理论模型预测结果的冲突,据此出现了两派有意思的讨论。第一,认为实证的数据库选择有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目前被广泛使用的EM-DAT数据库有关自然灾害中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保险索赔和新闻报道,而这些内容本身就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较富裕的国家在特定灾害中的货币损失会更高,保险覆盖范围与人均GDP高度相关,使得相关数据统计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会更加全面。Felbermayr和Gröschl(2014)基于地球物理和气象数据库的自然灾害强度数据,发现前1%的自然灾害使人均GDP减少6.83%,前5%的自然灾害会使人均GDP降低0.46%,与理论模型的预测相一致。第二,新的理论解释,即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创造性破坏”,提升经济的长期表现。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自然灾害摧毁了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导致短期产出水平下降,伴随着资本存量的补充,经济增速回归稳态水平。其中假定被摧毁的资本存量和补充的资本存量是一样的,但如果被摧毁的资本存量是旧的、缺乏生产力的,补充的资本存量是新的、更具生产力的,则自然灾害可能会反而提升了经济体的增长水平(Skidmore and Toya,2002)。 (2)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和大国外溢效应 在对各国经济周期联动性进行实证讨论的时候,大家普遍发现与G-7(或美国、欧元区)联系更紧密,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联动性越强(Kose et al.,2003)。虽然来自大国的溢出效应并不能算作共同冲击,但是对于中心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言,大国的一举一动所造成的冲击于众多小国而言就是共同冲击,会驱动各国经济周期的一致(Miranda-Agrippino and Rey,2020)。 首先,对于资本流动而言。根据国际经济周期模型,资本流动作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可以降低本国所受到的异质性冲击的影响,因而在资本流动频繁的国家之间,他们的经济周期会表现出更加一致的相关性。然而,Imbs(2006)提出了一种观点,正如卢卡斯之谜揭示出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资本流动在现实中可能会面临诸多维度的限制,并且资本流动可以具有羊群效应,因而实际的资本流动可能会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各国之间经济周期分歧加大。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金融联系和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关系非常的混乱。 针对这种混乱的结果,Kalemli-Ozcan等(2013a)的文章给出了一种解释,简单来讲就是把金融危机从外生冲击中单列出来,如果一个地区遭受的是生产力冲击(Real Shock;Productivity Shock),银行会减少在受影响地区的贷款,转而将贷款发放到那些没有受到影响的地区,从而造成“穷者俞穷、富者愈富”,加剧各国经济周期的差异性;如果一个地区遭受的是金融冲击(Financial Shock;Bank Capital Shock),即出现了金融危机,由于冲击了银行体系的资本金、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供给,金融体系运行的“底盘”受到直接冲击,从而银行会收缩业务,无论业务所在地区有没有直接受到冲击。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金融联系在日常可以平滑异质性冲击,但是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可能作为一种加速器将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传递至各个国家。Reinhart和Rogoff(2009)通过比较近8个世纪以来66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案例发现,大部分的金融危机都是由国内宏观经济因素所导致,如房地产泡沫、资本大量流入、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杠杆上升。随后爆发金融危机,然后通过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传导至各个国家,造成产出和就业的下滑。案例分析的问题在于所有的论述都是基于逻辑推理,理论分析中,Ueda(2012)构建了一个两国DSGE模型,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向企业提供跨境贷款,向投资者提供跨境借款,结果支持了案例分析的结论,显示出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使得一国的不利冲击传导至另一个国家。 除了金融危机,大国外溢效应还集中体现在政策的外溢性。于大国而言,本国的政策旨在解决本国的问题,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是一种共同的冲击。之所以大国的政策能够产生这么强的外溢性,核心在于全球金融的高度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使得单一国家的政策难以独立于全球核心国家的政策变动,Miranda-Agrippino和Rey(2020)发现全球金融周期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周期高度一致,但他们的研究更多地是描述性的。机制上,Bruno和Shin(2015)揭示了国际银行业的一种双层银行体系,即区域银行从国际金融市场(全球银行)借入美元,作为资本金支撑向当地企业提供贷款,全球银行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为区域银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此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升值,当地银行的放贷能力提升,同时伴随着当地企业(借款人)资产负债表改善,当地银行提升银行杠杆、发放更多地贷款。从而揭示了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美元币值影响全球各个国家的银行业杠杆,进而产生溢出效应。Gopinath和Stein(2021)关注美元作为主导货币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美元在贸易计价上的主导地位促使微观主体更愿意持有美元流动性,从而增加了对美元金融资产的需求,在美元抵押品不够的情况下就会吸引其他抵押品来满足美元抵押品的需求,导致UIP偏离和美元融资成本下降,美元融资成本下滑进一步刺激微观主体投资于美元项目和使用美元计价。美元在计价货币和安全资产上的主导地位相互强化,通过美元计价和美元融资将美国政策传导至其他国家。 (3)模仿效应 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一个异质性冲击仅影响某个特定的市场,不会冲击到其他市场,但是其他市场主体可能进行了错误的“联想”,使得冲击影响了自己的市场。这一渠道很早就被大家发现,例如Calvo和Mendoza(2000)定义的理性传染(Rational Contagion),他们提出随着金融全球化,投资者收集昂贵信息的收益更低,模仿其他市场优秀投资组合的成本低、效果好。各个国家市场的投资者相互模仿对方的投资组合,造成了各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早期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他们无法将这种模仿效应与基本面联系相区分,严谨的实证论证非常不容易。其中一种方式是在样本选择中强制剔除基本面因素的影响。Hasler and Ornthanalai(2018)试图论证新闻媒体可能在两个不同行业之间起到了风险传染的机制作用,他们使用Fama-French 48行业分类,并且通过COMPUSTAT里的客户-供应商关系数据排除相互联系的行业,最终识别出18个毫无关联的行业对。对这18个毫无关联的行业对进行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一个行业的关注度提升会增加这个行业的波动性以及不相关行业波动性,意味着不相关和行业存在回报和波动率的溢出效应。从而证实了作者的观点,即影响一个行业的负面冲击会通过新闻报道等渠道影响投资者的注意力,将其转移到其他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行业之中。 前文讲到冲击(或危机)传染可以通过基本面因素(如贸易、资本流动),也可能基于模仿效应(Social Learning;Social Imitation),后者主要是指传染发生在没有基本面联系或共同外部冲击的市场。但是两者常常是具有相互作用的,Hasler和Ornthanalai(2018)仅完备的证明了模仿效应的存在。还存在一种情况,现代媒体非常发达,当一国的投资者看到其他国家发生危机的事件后,会依据两个市场的共同信息采取行动,当其他国家的危机通过基本面因素传入本国后,本可以避免的危机因为投资者的行为而形成危机的自我实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每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和财政稳健度差异很大,但当主权债务风险来临之时,各国或者各个类别国家的债券会遭遇无差别的抛售,使得一些财政稳健的国家也深陷泥潭(Lane,2012)。 模仿效应不仅集中于投资者行为,也包括监管部门,在观察到其他国家采取的监管举措有效果之后,其他国家的监管部门也会采取类似的举措干预经济行为。例如,零利率下限(Bernanke et al.,2004)、央行货币互换(Aizenman,2010)。但是监管举措更多地是对既有经济状况的应对举措,而不是传导经济周期的主要力量。 4 思考和展望 两千多年前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原本是为了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战略意图,不会料想到自己意外打通的商路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丝绸之路”,更不会料想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千年之前,两个国家如何没有接壤,必然是各自发展而不会相互影响,现如今交易所中的价格变动可能在一分钟后使得大洋彼岸的公司破产。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的同时,我们对于经济周期传导的认知也在不停地更迭演进。 地理位置和经贸关系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两国接壤、经贸关系密切必然会造成两个国家的经济周期联动。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距离因素对于贸易成本的影响越来越小,产业链重构和转移的成本也逐渐降低。在新冠肺炎疫情事情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制造业品类的生产线可以在一个月内复制到一个全新的城市。与之相反,大国政策的外溢性在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脱离其他国家而独自快速发展,供应链网络、股权投资网络将各国、各个企业连接在一起,拥有先进技术、国际货币、政治话语权的大国就是这个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中心节点。大国政策会通过网络影响到全球的各个国家,如何防范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实行独立自主、有效的政策,也是中国政策当局亟待应对和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虽然资本管制、宏观审慎可以部分隔离外部政策冲击的影响,但并不是应对的根本之道,或许解决之法已经脱离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从系统的观念审视这个问题。 模仿效应是在信息化时代所独有的一种经济周期传导方式,发展迅速但尚未被监管部门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网络信息的传导速度不仅明显快于实体经济渠道,也快于金融渠道。甚至可能会出现,事件发生之后,监管部门还不知因何而来,最典型的案例即为金融诈骗。因而,我们要对海外的典型案例进行持续的跟踪学习,及时与国内的法律法规相对查,及时堵上可能存在风险的口子。当然,这种模仿效应也会出现在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进行沟通和交互的时候,一方面监管当局模仿国外部门的政策举措,可能会因微观主体事前的预期而降低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微观主体模仿国外主体的微观行为,倒逼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这种模仿和交互是当今信息化时代完全无法避免的现象,重要的还是加强中国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服务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