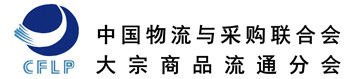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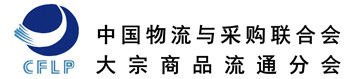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2023-07-21 来源: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换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需要在国际金融领域统筹谋划、系统施策,兼顾增长、效率与安全。具体而言,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值得高度重视。
一、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转变与资本账户开放
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国际收支可能发生以下结构性变化:一是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持续下降,甚至可能转变为经常账户逆差。主要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导致国内储蓄率下降、国内各种要素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持续升值等;二是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在顺差与逆差之间频繁波动;三是随着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干预程度的下降,外汇储备规模大致稳定。
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变化可能给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带来如下潜在影响:一是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缩小甚至逆转,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未来可能会更多地面临贬值压力;[1]二是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上升以及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可能明显上升,且跨境资本流动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将变得更为显著;[2]三是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将会面临新的转型压力。[3]
中国资本账户的后续开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前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考虑到未来十年内中国经济与金融面临的内外挑战,资本账户开放仍应秉持审慎、渐进、可控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还存在明显的优化空间。例如,中国央行应将以数量管理为主的资本流动管理转变为以价格管理为主,适时推出托宾税,且税率可以随着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相应调整。[4]又如,中国央行应该更好地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外汇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之间寻求权衡与配合。
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致经历了十年一个阶段的历程。1994年1月汇率改革的关键词是“汇率并轨”,也即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合二为一,实质是人民币汇率对外一次性大幅贬值。2005年7月汇率改革的关键词是“扩大波幅”,也即逐渐扩大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区间(由千分之三到百分之二)。2015年8月汇率改革的关键词是“中间价改革”,也即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开盘价)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总而言之,迄今为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程度也已明显下降。
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距离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或清洁浮动(Clean Floating)仍有一定距离。在激活逆周期因子之后,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依然较低。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终将走向自由浮动。从短中期而言,避免汇率大起大落冲击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依然必要。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加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程度以及提高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度,另一方面要避免汇率超调,因此,一种更为理想的过渡性汇率制度是为人民币有效汇率(例如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汇率指数)设置年度宽幅目标区。[5]只要人民币有效汇率没有达到年度波幅的上限或下限,央行就不对汇率进行干预。这种汇率机制能够更好地兼顾汇率的灵活性、透明度与基本稳定。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由美元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主要有三大缺陷:一是难以克服“广义特里芬两难”,也即为了向全球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美国必须保持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但由此导致的海外净负债上升在超过特定阈值后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元失去信心;二是中心国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产生了持续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三是俄乌冲突后的“美元武器化”行为降低了其他国家对美元资产安全和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安全的信心。[6]
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大概率将变得更加多元化或者碎片化。美元依然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但其各项全球占比指标可能进一步下降。欧元的国际地位有望保持稳定。人民币与其他几大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例如印度卢布)的重要性有望稳步上升。关于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更加稳定,这一问题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考虑到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表现出日益区域化本地化缩短化的特征,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趋势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碎片化趋势是基本匹配的。生产、贸易与金融的碎片化趋势可能提高韧性,但却是以降低效率为代价的。
迄今为止的人民币国际化表现出鲜明的周期性。2009年至2017年为第一个周期(其中2009年至2015年上半年为上升期,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为下降期),2018年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在第一个周期内,中国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可被概括为“旧三位一体”,也即推进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2018年以来,中国央行调整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这可被概括为“新三位一体”,也即推进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中国周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着力培养针对人民币的真实、粘性需求。[7]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爆发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挑战与新机遇,中国央行应顺应上述挑战与机遇,进一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调整。[8]
四、主权资产安全与全球投资战略
截至2022年底,中国拥有高达2.5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作为海外净债权人,中国面临以下三个福利问题:一是由于海外资产的收益率持续低于海外负债的收益率,导致中国持续面临海外投资收益为负的尴尬局面(2022年海外投资收益高达-2031亿美元);二是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并未充分转化为海外净资产;[9]三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日益盛行的“美元武器化”行为使得中国海外资产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如何更好地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呢?中国政府应在各个层面更加充分地实施多元化投资策略:一是海外资产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未来中国政府应该寻求更多地“藏汇于机构”,委托中外金融机构在全球开展金融投资;二是海外资产投资策略的多元化,未来中国投资者应该更多地投资于股权资产、大宗商品与另类资产;三是海外资产投资市场的多元化,未来中国投资者应该在更多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各类投资。[10]除此之外,加快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实现在更大程度上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绑定”,也有助于维护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
中国主权资产的全球投资战略应进行相应调整,尤其是应该与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结构性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在主权外汇资产管理领域,中国目前事实上形成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中投公司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三驾马车”格局。未来,在上述三个主体之间如何既实现一定程度的竞争以提高效率,又实现更多的互补与合作,需要进行统筹谋划。又如,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且当前社保资金缺口较大的现实,未来培育中国的海外主权养老基金是当务之急。主权养老基金既可以由现有机构(例如中投公司)转型而来,也可以设置全新的机构。
五、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重点考虑。问题之一是如何防范化解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之间的金融风险是相互之间密切关联的,因此需要出台一个统筹化解潜在风险的统筹方案。该方案必须经过周密的顶层设计才能够克服部门利益博弈导致的推诿与卸责问题。例如,要顺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既离不开新一轮债务置换(核心是中央政府加杠杆),也离不开精心设计的债务重组(核心是在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分担成本)。[11]在设计具体方案时,应考虑到东中西部的结构性差异。在防范化解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既要妥善化解潜在风险,又要避免扭曲激励机制从而形成更大的道德风险;二是应努力避免国内外风险同步共振现象的发生,这意味着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依然必要。
问题之二是如何为防范化解全球或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出中国贡献。首先,这需要构建更加完善以及覆盖更全面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核心机构,IMF的治理机制改革仍需继续推进以更加充分地反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其次,这需要促进更多层次与更加广泛的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设,例如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应该进一步完善。再次,构建更加公平以及能够更好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也变得日益重要。
六、夯实制度保障
深入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中国国际金融方略的最重要制度保障。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增长效率的趋势性下降。要提升增长效率,就必须大力推动各类结构性改革。目前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一是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大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二是努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落地见效;三是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速推动土地流转改革;四是积极推动要素市场化定价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实现高质量、制度性对外开放是新时代中国国际金融方略的另一重要制度保障。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把目前国内数量众多的自贸区自贸港做深做实。迄今为止,国内众多自贸区存在建设方案高度雷同、彼此存在低水平竞争、缺乏实质性开放举措、缺少系统性政策抓手等问题。各自贸区、自贸港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与利益诉求,各自试行不同的开放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力与协同效应。[12]例如,在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可以考虑在香港、澳门、上海自贸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自贸区、海南自贸港之间进行较高层次的统筹,从而既避免重复建设与低水平竞争,又能相得益彰共促发展。
(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