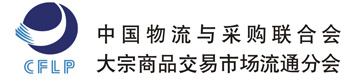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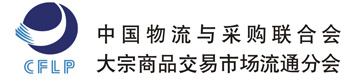
2017-03-09 22:07:06 来源:第一邮币卡
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去监管”,以及中国“一行三会”的所谓“强监管”,成为国内市场方面热议的议题。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去监管”、还是“强监管”,其实都是伪命题。因为,当局的政策监管,总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监管、法治,又是从立法到司法、再到执法的法制或法律体制的系统建设为法理基础的。不是吗?仅就政策的“法理基础”而言,2017年2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指出:“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
因此,对于目前因“强监管”而令得国内商品现货市场投资人、从业者沉浮不定而举足失措的业内来讲,以上述“政策思路”为基本点,面向“以法治市”的方向去进行自身市场的建设,并据此有理、有节、有利地寻求政策监管及当局,对业内建设发展给予积极的促进和保护,就变得极具战略意义的发展策略了。为此,笔者谨从——政策监管的行业针对性与市场同一性;市场自律组织与部门主管、金融监管部门的互动性;诸市场及其行业自律与政策监管的法理性;市场监管的专业化、制度化——这四个方面,分上、下两篇来给予较为系统而简要的阐述。
首先,政策监管的行业针对性与市场同一性。
无论是长效政策性监管,还是短时期的监管政策,在政策框架下的监管,应要强调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对监管的方向性、成效性的影响。以商品市场中的所谓现货、期货市场而论,由于现货市场所服务的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其所具有的分明、具体的行业属性,远较期货市场多样、复杂得多,因此,现货市场政策监管的差异化、区别性,也就远比期货市场“标准化”、统一性,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恰恰也是考验政策监管针对性到不到位,并因其监管是否到位、而产生其政策监管时效性强弱的关键。
同时,因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而使得从商品到资本市场的日益金融化,则是市场政策监管所需要的同一性的重要原因。而这个重要原因,也同样反映在商品市场领域的现货市场方面。因为,最“起码”在商品现货、期货市场对冲交易方面,也必然导致在利用流动性、这一同一性的金融工具或金融资本时,产生极其容易混淆的、有意或无意的概念或逻辑“混乱”。因此,在研究、讨论市场政策监管的行业部门与监管部门的市场治理权责谁主、谁辅的所谓监管主体之时,一定要首先确定市场参与主体,究竟有谁或由那些参与主体构成了其市场,再基于这样的市场参与主体来明确监管主体,并进一步地厘定、厘清政策监管的方方面面,才是正本清源的政策监管之道。
此外,基于商品现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方向,是为了促进有关地区和行业的商品生产流通及其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也应当或更应当依据有关地区、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方向——如地区或行业五年规划等,来从事其自身的商品现货市场建设,并也因此而接受有关地区、行业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所给予的针对性与同一性相结合的政策监管。这样的一方面基于现货商品生产流通需要的市场建设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又基于市场建设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即具有针对性、又具有同一性的市场监管,恰恰是商品现货市场所归属的地区、行业,进行有效的分业监管的重要内容,不可偏残或不可或缺、并亟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保证。
其次,市场自律组织与行业主管及金融监管部门的互动性。
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为社会管理体制、核心的国家,因此,所谓的自律性组织的行政化,免不了与其市场化所带来的种种权利需求,产生政策性——甚至法制性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是需要深化的社会体制改革来给予制度性的保障的。同时,也是基于商品现货市场上述政策监管的行业针对性与市场同一性的实际需要,各个服务于自身地区、行业商品生产流通的现货市场,因此,对于国内的商品现货市场来讲,其自律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及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互动性监管体系的建设,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此外,从更为综合或系统性的社会体制来看,虽然政府简政放权到行业组织的行政化、社会化管理趋势日益明显,但是,与此同时也显现出所谓的市场及行业“自律”的公信力的不足。同时,在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利益共同体方面,也因应有关市场自律组织的“经济基础”的不牢靠或不稳固,而使所谓的市场及行业“自律”的资信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此,公信、资信不足,又哪里来的信用呢?没有信用,又怎么能够落实得了自律呢?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直接、具体服务商品现货市场整个行业,而组织建立起来的所谓自律组织,也应当基于自身所服务的行业、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实际诉求,对有关的政策性监管——甚至包括法治性监管,具有相应的、从理论及实践方面给予主动反映的话语权和代表权,而不应当仅仅是或成为被动的政策监管的代言、代行组织。
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有关经济社会管理“自治组织”公信、资信及权力的不足或缺憾,商品现货市场所需要的行业主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与这一市场所涉及的行业及地区的所谓自律组织的、有关社会管理方面的互动,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客观、系统而科学地给予加强了。在此仅仅就商品现货市场来讲,这样的互动性,至少是三位一体的:一是市场及其行业的自律组织;二是市场所服务的实体产业领域的行业主管部门;三就是伴随市场所引入的流动性进来而来的金融监管部门。否则,商品现货市场的同一性及其“一刀切”的“清整”容易,但其市场政策监管的针对性、时效性,必然大打折扣,并饱受公理性、法理性的诟病——甚至包括“体制内”权力要求所造成的制度性内耗的侵蚀、损害。
第三,诸市场及其行业自律及政策监管的法理性。
人文历史及社会生产关系的传承与变革;现实及未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建设的需要;依据宪法致政的所谓宪政,以及基于宪法这部根本大法所建立起来的、从刑法到民法的整个法律体系——当然也应当包括“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那一项制度和那一部法律——更不用说政策,不是依据相应的法理基础,来给予建立、修订及完善的呢?如此深层次或顶层、顶顶层的制度及法律建设尚且如此,那么,基于上述传承、变革及需要的所谓行业自律、政策监管,又怎么能够没有自身所依据的法理性呢!
真所谓法理不外乎情理,情理不外乎人情。所谓的法理或法理基础,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活的物质与社会要素——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物质与社会要素——劳动力的主体——人,对社会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及对社会生产资料诸要素,所寄予的、从个性到共性的物质与社会生产及生活的需求或追求。无论什么样的组织和什么样的人,也无论这些组织和人以什么样的权力或权利,剥夺、侵害了这样的需求或追求,都是违背人情、情理及法理的行为。而以这样的行为所建立的自律、监管及法律的制度,自然也就失去了其法理或法理基础,并由此从上层建筑方面损害、甚至摧毁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
此外,仅仅就法律框架下的市场监管而言,也要强调政策监管在立法、司法及执法的法理基础上或法律制度下的法理性。因为,政策监管本身,至少就存在对政策把握的张驰度,以及监管当局所存在的政策实施的态度等人事、“人治”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受中国社会传统的、以行政为主导的社会管理观念和行为所牵引,而导致政策对市场监管的张驰不定、宽严失据的问题。从而,一方面导致市场对政策监管的投机盛行,另一方面则导致政策所赋予的监管权力,获得了相应空间的权力寻租的权利。其最终结果,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市场本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严重损害了政策及监管当局的公信力。
最后,市场监管的专业化、制度化。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脱实向虚”的共同的监管办法。可能是先立足于最基本的标准,统一起来,标准特别高。不过,以笔者愚见,无论是监管办法的标准高、低,其统一性、时效性和普惠性,则尤为重要。这也就是要求对市场监管的政策及政策监管的本身,也需要“标准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而其中的这个政策监管的“标准化”,实际应当是政策监管的制度化、法制化。这样的政策监管的制度化、法制化,也应当是与政策监管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否则,一定会因政策监管的不断行政化,而步入监管的官僚化。而一旦政策监管步入官僚化,那么,其离政策监管的公权力被滥用,并进而形成形形色色的权力及权利腐败,也就不远了。
如此,首先也就涉及到有关市场监管的专业化问题而言。而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及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必须的、从商品价值到资本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的生产流通入手,去从其基本的理论与实践“常识”方面,给予客观、系统而科学的阐释。比如权益市场中商品权益与资本权益的权益结构及需求的异同;比如商品与资本市场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市场交易及流动性需求的异同;比如包括商品、资本在内的金融市场资管中实业投资与流动性投资及其资本经营管理方式及需求的异同。如此等等地从所谓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的矛盾统一中,彰显市场监管及监管政策的专业化水平或程度。
其次,再从涉及到的、有关市场监管的制度化问题来讲。无论是从小到家庭、企业,大到行政区划、国家来讲,其社会的人事内耗,固然可怕复可恨,但是,其社会制度内耗,则更可怕、更可恨且危险。这正如一个市场因制度建设不到位,而导致市场内幕交易丛生、行情波云诡谲一样,诸多的所谓市场政策监管制度的上下僭越、左右互博,也必然导致所谓的市场监管及其监管政策,形成官商勾结、弱肉强食的权利寻租工具。如此,它不仅仅严重危害市场各个参与主体的“身家性命”,也危害市场及社会的利益共享、长治久安。如此可知,所谓制度化的监管,不仅包括监管制度及政策制度、法律制度,更包括涉及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诸领域的种种社会制度。
如此可知,2月2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强调的“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市场本身的监管呢……
来源:第一邮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