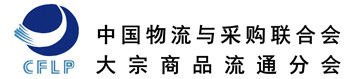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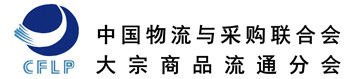

2024-10-10 来源:
摘要: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融合,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是当前国内外统计机构与研究学者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提炼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形成要素,构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界定数字经济核算范围,确定数字经济产品,筛选数字经济产业,对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进行测算,并将测算结果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53028.8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6%;数字经济总产出147574.05亿元,占国内总产出的6.53%。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8.12%;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美国0.44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2.77%,占GDP比重低于美国0.77个百分点,略高于澳大利亚0.03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4.43%,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8.27%,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本文深化了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研究,系统监测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与结构,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和提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一、引言
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的诞生和发展是迅速成长的现代信息技术与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等相融合的结果。近年来,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在国际经济中争夺话语权而抢占的制高点。欧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中国、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陆续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中国2016年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都强调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作出重要指示;美国自2010年后制定的国家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超过5项。数字经济已成为信息时代下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发展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亦是新经济背景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数字经济改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提供了更加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近些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没有显示出预期的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逐渐讨论是否出现了“新索洛悖论”:随处可见的数字经济却唯独在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中无法捕捉到。一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不能捕获到那些由数字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效率提升,GDP及其他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也许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统现象(The Mis-measurement)。那么,当前统计机构对数字经济是否存在着测度不充分的现象,数字经济是否造成了GDP的漏统,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等的推动作用到底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均需要对数字经济的规模做出准确测度研究后来解答。
数字经济规模测度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国际组织、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有关学者的重视。各方面对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不尽相同,本部分对有关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旨在系统地把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测算工作奠定基础。纵观国内外对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按照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大体可划分为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方法论研究、增加值测算研究、相关指数编制研究和构建卫星账户研究等。
在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方法论的研究方面,从国际上看,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OECD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EC)在《国民账户体系(2008)》(2008年SNA)中对涉及数字经济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修订;OECD(1996,2011,2012,2015)先后提出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的测算框架;有关学者认为,从概念的角度,GDP已经捕获了数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增加值(Ahmad and Schreyer,2016),数字经济的漏统不是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唯一原因(Ahmad et al.,2017);Diewert and Fox(2016)定义了福利测度的框架,关注数字化产品与福利变化的影响;也有一批学者对免费数字内容核算方法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Brynjolfsson and Oh,2012;Leonard et al.,2016;Brynjolfsson et al.,2017)。在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信息产业投入产出表模型(贺铿,1989;王中华,1989);指出网络经济不仅是产业层面的经济,提出国民消费总值(GNC)的测算方法(杨仲山,2002);对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以及知识产业的划分进行了研究(魏和清,2005);系统梳理和比较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型经济的测度方法(张美慧,2017);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个角度详细地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名义产出水平核算带来的挑战,总结了数字经济对物价指数核算的挑战,提出了数字经济与相关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潜在方向(续继和唐琦,2019);系统研究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统计的若干重点研究领域,从新经济概念界定和行业分类、新经济统计调查方法、新经济就业与收入统计、新经济增加值核算等方面对新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进行详细的探讨,并从经济、社会、环境等角度分析了大数据在中国绿色发展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许宪春等,2019b;2019c)。
在增加值测算研究方面,Machlup(1962)和Porat(1977)开启了测算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增值的研究方式。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有关国际组织、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有关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对数字经济范围进行了界定,并且利用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Barefoot et al.,2018;BEA,2019);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借鉴BEA的测算方法,对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程度进行测度(ABS,2019);新西兰统计局(Stats NZ)在借鉴OECD数字经济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测算得出,2007—2015年新西兰数字订购产品总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20%(Stats NZ,2017)。加拿大统计局测算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口在2017—2018年购买了音乐和视频下载以及流媒体服务(Statistics Canada,2018)。一些国际咨询公司也对部分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了测算(Knickrehm et al.,2016;Dean et al.,2016)。在国内,相关学者在借鉴Machlup-Porat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2002—2005年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康铁祥,200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也有学者在借鉴OECD数字经济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字促成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进行了测算研究(向书坚和吴文君,2019)。总体看,由于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测算范围和测算方法均未统一,使得测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OECD数字经济研究框架和BEA对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已对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官方统计机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相关指数编制研究方面,小松崎清介等(1994)开启了“信息化指数”测算的研究方式。在此之后,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和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日本电信与经济研究所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信息化指数模型;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了一套评价七国信息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编制了新经济指数(ITIF,2014);OECD(2007,2014)构建了ICT与数字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欧盟统计局(Eurostat)编制了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DESI),DESI成为反映欧盟各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进程的重要工具和窗口(Eurostat,2017);WB编制了知识经济指数(Knowledge Economy Index,KEI),KEI研究覆盖国家数量达到146个(WB,2010);有学者在KEI的数据和估计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知识经济指数(Digital Knowledge Economy Index,DKEI)(Ojanpera and Graham,2017)。在国内,有许多学者采用信息化指数方法来测度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水平(靖继鹏和王欣,1993;杨京英等,200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编制了数字经济指数(Digital Economy Index,DEI),力图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进行观测和反映;近期,有学者构建了国家数字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对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数字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吴翌琳,2019)。
在卫星账户构建研究方面,有关国际组织、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学者主要开展了构建ICT卫星账户和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igital Economy Satellite Account,DESA)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澳大利亚统计局(ABS,2006)、智利统计局、南非统计局已经建立了ICT卫星账户,马来西亚统计局2009年开始编制ICT卫星账户,2011年在ICT卫星账户的基础上引入一系列辅助指标,共同构成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卫星账户;OECD成立数字经济下GDP测算咨询组(Advisory Group on Measuring GDP in a Digital Economy),提出数字贸易维度框架与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框架,并尝试性编制DESA的供给使用表(OECD,2017a,2017b);Barefoot et al.(2018)界定了数字经济范围,并基于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为美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屈超和张美慧(2015)提出了构建ICT卫星账户的构想;杨仲山和张美慧(2019)系统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编制问题,并构建了数字经济静态总量指标与数字经济直接贡献指标。
相较于增加值测算和相关指数编制的方法,数字经济卫星账户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各行业从事数字经济特征活动的情况,是测度数字经济实际发展规模及其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程度较为可行的方法。然而,目前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受现有统计数据的限制,较难实现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实践编制。OECD(2018)建议,现阶段可以先计算数字经济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实践编制奠定研究基础。对数字经济增加值进行测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BEA的研究(Barefoot et al.,2018;BEA,2019),为美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建立奠定基础,ABS(2019)也借鉴BEA的测算方法对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增加值进行测算,可见BEA的测算方法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通过该方法测算得出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和结构也将具有较强的国际可比较性。
纵观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有关国际组织、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待完善之处:一是数字经济统计范围有待准确界定;二是数字经济统计分类有待清晰划分;三是数字经济测度方法有待深入探索;四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字经济规模有待准确测算。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系统梳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界定数字经济的内涵与范围,筛选数字经济产品,确定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建立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对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并将这些测算结果与BEA、ABS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以期对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与结构及其与美国、澳大利亚数字经济的差异进行客观反映,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框架、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编制进程和制定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本部分系统回顾国际上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梳理上述经济模式的特征及内涵要素,结合当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尝试对数字经济的范围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分类的研究经验,提炼不同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对数字经济分类的划分逻辑与标准,借鉴联合国统计署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的分类原则,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依据,结合“分”与“合”的“双向复合分类”机制,尝试对中国数字经济进行产业划分,并对数字经济测度方法进行初步的对比与探讨,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奠定基础。数字经济核算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1. 数字经济演进历程
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研究经历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以及数字经济的探索过程。
(1)信息经济。信息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信息产业到信息经济的发展过程,信息产业的主要代表是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产业,伴随着ICT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融合,ICT向社会、经济、生活等领域的渗透作用逐渐增强,由此产生了信息经济模式。Porat(1977)出版了《信息经济》一书,界定了信息活动、信息资本、信息劳动者等与信息经济相关的基本概念和范畴。《OECD信息技术展望》(OECD,2010)系列出版物,分析了ICT产业发展趋势与发展动态,对ICT部门与全球化、ICT技术与就业、互联网经济、ICT与绿色增长等方面进行研究,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信息社会测度指南》(OECD,2011)系列出版物,围绕ICT产品,ICT基础设施,企业、住户及个人对ICT的需求情况,内容与媒体产品等方面对信息社会测度展开系统研究,为ICT研究领域的学者、分析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标准参考与建议,是从供给与使用层面刻画信息社会较全面的统计框架。总体看,信息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信息产业发展规模的大幅度提升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融合,信息经济的核心内容仍为ICT产业与ICT产品。
(2)互联网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逐渐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各领域快速发展不可替代的要素。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保障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它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与电力、水利、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相似。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经济”这一名词逐渐兴起并广泛传播。从2010年开始,OECD运用《互联网经济展望》替代了《信息技术展望》,对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企业、政府和个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数字内容的发展,互联网安全与隐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OECD指出,互联网经济是快速演变的,且其发展方式在不同国家存在一定差别。相较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体现在信息通讯技术的跃迁及其与经济运行的更充分融合。在互联网经济的背景下,产品的范围进一步拓宽,衍生出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传播的电影、音乐、新闻、游戏、广告等无形数字内容产品。
(3)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一词是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数字经济描述的是一个广泛运用ICT技术的经济系统,包含基础设施(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计算能力与安全服务)、电子商务(在前端与后端大幅利用ICT的商业模式)以及运用ICT的B2B、B2C和C2C交易模式。Negroponte(1996)发表著作《数字化生存》,指出数字化生存是由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等对人类生产生存方式带来巨大变化进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日本通产省于1997年5月开始使用数字经济这一名词,其认为数字经济是需要具备以下四种特征的经济业态:①使不存在人员、物体和资金转移的非物理移动型经济成为可能;②合同签署、价值转移和财产积累可通过电子途径完成;③信息通讯技术高速发展;④电子商务广泛发展,数字化逐步渗透进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OECD(2017a)指出,随着云计算、机器学习、远程控制、自动机器系统的出现,物联网技术逐渐成熟,使ICT与经济之间的融贯联系大幅度增加。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并渗透进世界经济运行的多个方面,包括零售(电子商务)、交通(自动化车辆)、教育(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健康(电子记录及个性化医疗)、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社交网络)等领域,数字化创新和新型商业模式引领了社会工作和贸易方式的转变。
由此可见,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对不同时期新型经济业态的描述,三者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仍是信息技术。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融合程度逐渐增强,衍生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逐渐增多,数字经济更能体现当前新型经济的发展特征。
2. 数字经济内涵与形成要素
(1)数字经济内涵。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日益跃迁的信息技术紧密相连,动态发展特征使得数字经济内涵界定比较困难。数字经济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内涵不断丰富。当前的数字经济正处在快速演变、与国民经济运行全面融合的阶段,人们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认识目前很难统一。
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理解是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产业经济,数字化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消费与分配活动需从依附于传统国民经济活动的部门中剥离出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独立的核心产业,即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产业主要包括以信息为加工对象,以数字技术为加工手段,以数字化产品为结果,以国民经济各领域为流通市场,其本身没有明显的利润,但可显著提升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利润的公共性产业。持这类观点的代表国家有法国等。法国数字经济监测中心认为,数字经济是依赖于ICT的行业,认为数字经济是电信行业、视听行业、互联网行业、软件行业以及需要利用上述行业来支持自身运行的行业的集合。网络经济产业、通讯产业、软件产业、卫星产业等均属于数字化产业的范畴。由于数字经济本身发展的特征,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诠释经历从狭义到广义的过程是具有必然性的。广义的理解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持这一类观点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和韩国,2016年中国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认为“数字经济指的是以数字化信息与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网络为载体,以ICT的使用来促进效率提升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活动总和”。俄罗斯联邦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保障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为目的在生产、管理和行政活动等过程中普遍使用数字化或信息化技术的经济活动。而韩国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则更加宽泛,将其定义为以互联网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而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可见上述三个国家均将数字经济的内涵理解为基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只是在侧重点上稍有不同。
(2)数字经济形成要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因素分别是:数据和数字平台。数字平台又可以分为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交易平台是以在线基础设施支持多方之间交换的双边或多边市场,创新平台以操作系统或技术标准的形式,为代码和内容制作者开发应用程序和软件创造环境(UNCTAD,2019)。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数字化技术演变到数字化产业,更进一步形成数字化经济活动的过程,目前已经逐渐趋近于成熟。数字经济是现代数字化技术与国民经济运行各方面紧密结合的产物,数字经济代表着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平台为主要媒介、以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是,数字化技术充当数字经济中的代表性技术角色。广义的数字经济不仅包括数字化交易,还应将保障数字化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数字化媒体以及数字化货物与数字化服务等包含在内,进而构成了多层次全面的数字经济运行系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广义数字经济形成要素:①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电信设备等支持数字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是确保数字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②数字化媒体。数字经济的重要形成要素为数字化媒体。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知识必须通过物理手段进行传递,包括信件、报告、现金、支票、收据、面对面会议或电话等,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些事务一旦被数字化,知识、内容或信息便可以光速从一个位置传输到另一个位置,从而消除了由时间和距离引起的许多通信障碍。数字化媒体包括直接销售型数字媒体、免费数字媒体和大数据数字媒体等。③数字化交易。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网络背景下使更多的交易方式成为可能,人们通过网上交易的方式获取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或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对数字化交易类型的准确划分与把握对理解和测度数字经济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OECD对数字化交易类型进行了划分,包括数字订购、平台实现与数字交付三种方式。④数字经济交易产品:货物、服务、信息/数据。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对这种经济活动的交易产品确认也相当重要。2008年SNA将产品类别在货物和服务的基础上引入知识载体产品的概念,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与“数据”也成为具有交易价值的除货物和服务之外的单独产品(如图2所示)。

数字经济规模核算的步骤主要包括:界定数字经济范围;筛选数字经济产品与数字经济产业;确定核算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数字经济总产出等指标的规模。前三个步骤主要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的建立,其对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部分将对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进行系统研究,为数字经济规模的实际测算奠定基础。
1. 数字经济范围
借鉴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经验,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应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1)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Digital Enabling Infrastructure)。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是确保数字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OECD、BEA和马来西亚统计局在数字经济概念框架研究中,均将此项内容纳入数字经济的范畴之中,可见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主要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电信设备等支持数字经济运转和发展的基础设施。
(2)数字化媒体(Digital Media)。用户在数字化设备以及社交平台、音频网站等创建、访问、存储或浏览的内容即为数字化媒体,数字化媒体的出现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一项重大革新。数字化媒体包括:①直接销售型数字媒体,企业向消费者销售数字产品或提供数字产品的预定服务;②免费数字媒体,一些公司免费向消费者提供数字媒体,例如优酷或Facebook等社交网站,这些提供免费数字媒体的网站通过收取广告费用来盈利;③大数据数字媒体,一些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产生了高维度的数据资产,公司对消费者行为和特征等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可以通过销售数据资产来盈利。
(3)数字化交易(E-commerce)。交易方式的革新是数字经济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OECD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框架主要侧重于解析数字化交易本质,数字化交易在数字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关于数字经济交易类型的准确划分与把握对理解和测度数字经济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OECD对数字经济交易类型进行了划分,包括数字订购、平台实现与数字传递三种方式,按照交易主体与客体的机构单位类型的不同,数字化交易则可分为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消费者(B2C)以及个人对个人(P2P)等的交易类型。
(4)数字经济交易产品(Digital Economy Trading Product):货物、服务、信息/数据。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交易产品的确认也相当重要。2008年SNA在产品类别中新增了“知识载体产品”类别,调整过后的产品类别中包含货物、服务与知识载体产品,其中,货物是指有某种社会需求且能够准确确定所有权的有形实体,服务是指生产者按照消费者的需要进行活动而实现的消费单位状况的变化,知识载体产品是指那些以消费单位能重复获取知识的方式而提供、存储、交流和发布的信息、咨询和娱乐。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载体产品是交易中的重要对象。UNCTAD在《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数字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OECD(2017b)提出数字经济概念框架,在数字经济交易产品的范围中也单独添加了“信息/数据”这一项,可见信息/数据这类具有知识载体性质的产品是数字经济交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所以本文界定的数字经济交易产品包括货物、服务、信息/数据这三项。
2. 数字经济产品与数字经济产业
在对数字经济内涵做出界定之后,接下来的步骤是对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产品进行筛选,中国统计上运用的产品分类为《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国家统计局,2010),共包含97个产品类别,每个类别下对应数量不等的产品小类。《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是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构建的产品目录,97个产品类别分别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门类下的大类,共计97大类。接下来,根据数字经济包括的四大组成部分,从《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逐一筛选数字经济产品,并进一步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确定生产该产品的产业,为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做准备。
值得说明的是,数字经济中包含了所有数字化的货物和服务,然而在《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部分产品同时拥有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的成分,这类产品被称为“不完全数字化产品”(Partly Digital Product),从这类产品中剥离出数字化的成分需要更多详细的数据作为支撑,而目前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基础数据还不够完善,因此,不能对这类产品的数字与非数字化内容作出准确划分,考虑到结果的准确度,本文在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中,只包括了完全或主要特征为数字化的产品。
(1)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品及对应的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指的是支持计算机网络及数字经济存在和运转的物理设施等,包括的产品有计算机硬件、软件、电信设备等。表1中列出《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符合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特征的产品及生产这些产品对应的产业。

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中还包含了为数字经济运营提供场所的建筑物和具有嵌入软件能够联网的汽车或其他设备等,但是这两类设施可以同时用于数字经济活动和非数字经济活动,将其中用于数字经济活动的部分准确筛选出来是相当困难的,目前还没有充分的数据支持。因此,本文只考察了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的电信设备与服务、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部分,这三部分也与BEA的测算范围一致。
(2)数字化媒体产品及对应的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媒体指的是用户在数字化设备上创建、接触、储存或浏览的内容。在BEA对数字化媒体产出和增加值的估计中,将数字化媒体划分为:数据流服务、互联网发行和互联网广播三个部分。表2中列出《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符合数字化媒体特征的产品及生产这些产品对应的产业。

数字化媒体中还包含了免费数字媒体,提供免费数字媒体的企业通常通过广告费用来盈利,对免费数字媒体价值的估算需要详细的与免费数字媒体相关的广告收入数据与其他相关财务数据的支持,目前这部分数据还较难获取,所以没有把免费数字媒体纳入数字化媒体的核算范围之内,本部分筛选的数字化媒体产业与BEA数字化媒体测算范围相对应。
(3)数字化交易产品及对应的数字经济产业。BEA认为,从广义上讲,所有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货物和服务交易都属于数字化交易,即电子商务。数字化交易包括通过数字订购,平台实现或数字传递进行的交易和相关的网上贸易代理活动,按照交易双方机构单位类型的不同,数字化交易可以划分为B2B、B2C、P2P三种类型。受现有数据的限制,BEA未对P2P类型交易的发展情况进行测算。表3中列出《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符合数字化交易特征的产品及生产这些产品对应的产业。

根据《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国家统计局,2018)中对电子商务的界定,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电子商务活动包括三种类型: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动;②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货物)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台内经营活动;③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货物)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活动。
由于电子商务活动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多个不同门类和大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按其主要活动归入相关行业类别,如网上房地产中介列入7030(房地产中介服务),网上铁路、民航等客运票务代理列入5822(旅客票务代理)等。对包含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小类中的电子商务活动进行准确筛选和测度均存在较大的难度,进一步考虑到与BEA测算结果的国际可比较性,本部分对数字化交易相关产业的筛选包括了B2B批发和B2C零售两个方面。
(4)数字经济交易产品及对应的数字经济产业。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产品均可以通过数字化交易的方式成为数字经济运行中的一部分,而就数字产品本身而言,是数字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产品包括数字货物、数字服务与数据/信息。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与“信息”均具有了产品的属性,是数字化交易中的重要参与者。生产数字化产品的产业与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业存在较大的重合。因此,为避免重复计算,本文没有单列生产数字经济产品的产业分类,认为其增加值已经包含在了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业的增加值之中。
3. 核算方法
在确定了数字经济的范围之后,通过统计用产品目录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筛选出数字经济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国民经济行业,进而测算上述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总产出、增加值等总量指标。借鉴BEA的测算方法(Barefoot et al.,2018;BEA,2019),假设数字经济中间消耗占数字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与相应产业中间消耗占总产出的比重相同。由于现有数据不能提供数字经济各相关行业的详细数据,因此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总量指标测算所需要的大部分数据需要估算。在估算过程中需要借助的工具系数有以下几种:
(1)行业增加值结构系数。根据数字经济内涵筛选出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渗透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及其子类中。现有的统计资料主要提供门类层面上国民经济行业增加值数据,《中国投入产出表》提供了相对详细的139个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无法完全确定属于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以及更加细分类别的增加值数据。需要引入“增加值结构系数”来推算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数据,可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行业ij增加值为第j行业第i子类增加值,行业j增加值为行业j子类的增加值合计。
(2)数字经济调整系数。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国民经济行业中,一些行业只有部分内容属于数字经济,例如,批发业中的互联网批发、零售业中的互联网零售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所有行业增加值加总来计算数字经济总增加值。参考郑彦(2017)与黄璆(2017)构建“教育调整系数”和“物流调整系数”的方法,本文引入“数字经济调整系数”,数字经济调整系数是指行业中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该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3)行业增加值率。行业增加值率是指国民经济各行业增加值与相应行业总产出的比率,可用公式表示为:

![]()
借鉴BEA的估算方法,假设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中,数字经济中间消耗占数字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与其所属行业中间消耗占总产出的比重相同,即各行业数字经济增加值为该行业数字经济总产出与该行业增加值率的乘积,可用公式表示为:
![]()
结合公式(3)与(4),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通过上述阐述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调整系数既是行业中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该行业总增加值的比重,也是该行业中数字经济总产出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重。
本文结合现有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借助行业增加值结构系数、数字经济调整系数与行业增加值率等指标,对中国2007—2017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指标进行系统测算。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发酵的背景下,对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和结构进行比较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BEA在2018年对2006—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做出估算(Barefoot et al.,2018),2019年对美国1997—2017年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更新(BEA,2019),ABS借鉴BEA的测算方法对澳大利亚2011—2016年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ABS,2019)。本文在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与BEA和ABS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利于客观理解中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
1. 分行业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
(1)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增加值测算。如前所述,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包含计算机硬件、软件、电信设备与服务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生产上述产品的产业包含门类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全部内容与门类C“制造业”中的第39大类“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即制造业门类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结构系数,根据对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业的筛选,上述比值也代表了“制造业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由于《中国投入产出表》不是每年更新,本文借助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与延长表)的相关数据,得到上述年份的制造业数字经济调整系数,其余常规年份的数字经济调整系数则可通过现有年份数据进行估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通过已知年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两者相比得到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7年的制造业数字经济调整系数,对2007—2017年制造业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缺失值进行估计并结合制造业增加值数据,得到2007—2017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将其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加总,得到2007—2017年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增加值。
(2)数字化交易增加值测算。数字化交易增加值是数字经济增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均对数字化交易总增加值做出了估算。根据上文对数字化交易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的筛选,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数字化交易对应的行业包含门类F“批发和零售业”中的“互联网批发”“互联网零售”和“贸易代理”3个小类。
借鉴BEA关于电子商务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假定数字化交易相关产业总产出占批发和零售业总产出的比重等于数字化交易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的比重。本部分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的数据,将互联网批发、互联网零售业和网上贸易代理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占批发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互联网批发、互联网零售业和网上贸易代理总产出之和占批发和零售业总产出的比重,从而得到批发和零售业的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结合历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数据,得到2007—2017年数字化交易增加值数据。
(3)数字化媒体增加值测算。数字化媒体产品的增加值计算即生产数字化媒体产品相应产业的增加值核算,通过对国民经济行业中生产数字化媒体产品相关产业的筛选,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数字化媒体对应的行业包含门类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的第87大类“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以及“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数字出版”3个小类,还包含门类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搜索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其他互联网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和“信息处理和储存支持服务”6个小类。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如下:先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估算“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结构系数,然后利用该系数结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估算2007—2017年“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增加值。“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与“数字出版”3小类增加值测算,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测算普查年度3小类营业收入占“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假设该比重等于3小类增加值占该门类增加值的比重,并认为短期内比重不变,结合历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数据,得出“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与“数字出版”3小类的增加值之和,进而得出数字化媒体增加值。
2.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国际比较
(1)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结合上文对数字经济各组成部分增加值的测算结果,汇总得到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增加值规模及其占历年GDP的比重(见表4)。

测算结果显示,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加值占历年名义GDP的平均比重约为5.15%。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7—2017年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2012年后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呈现快速上升的走势。
现将本文的测算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的一些测算结果进行比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不同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测算结果显示,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11.5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9.28%;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4.0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2.80%。向书坚和吴文君(2019)研究显示,2017年,中国数字促成产业和广义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之和为161463.4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9.52%。埃森哲围绕ICT基础设施、ICT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渗透率四部分,测算得出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0.50%(Knickrehm et al.,2016),波士顿咨询聚焦互联网相关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方面,测算得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90%(Dean et al.,2016)。
通过对比可知,由于测算范围和测算方法的不同,上述研究对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的测算结果普遍高于本文的测算结果。由于本文的测算范围和测算方法充分借鉴了BEA和ABS的研究经验,采用较为“保守”的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范围和方法,使得本文对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的测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国际可比较性。本文测算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2388.06亿元,占中国GDP的比重为5.73%,根据Barefoot et al.(2018)、ABS(2019)和BEA(2019)的测算结果,同年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为120.92百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50%,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增加值为9.35百亿美元,占澳大利亚GDP的5.70%;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53028.85亿元,占GDP的比重已达到6.46%,同年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为135.13百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90%。
(2)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增长率。参考许宪春(2004,2019a)对不变价GDP生产核算计算方法的相关研究,对中国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不变价增加值进行计算,将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如图3所示)。通过对2008—2017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可知,2012年后,数字经济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2017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为6.90%,同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增长率达到26.10%,该增长率达到观察期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增长率的最高值。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促进中国GDP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

进一步将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根据Barefoot et al.(2018)和ABS(2019)的测算结果,2006—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5.60%;2012—2016年,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50%。本文测算结果显示,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4.43%。
(3)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变化情况。2007年,中国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的增加值占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比重分别是91.33%、5.66%和3.01%。2017年,这三个部分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分别为90.11%、6.25%和3.64%。可见,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增加值规模较大,占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数字化媒体与数字化交易增加值的规模较小,占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比重存在上升趋势。2017年,美国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4.60%;数字化媒体与数字化交易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为15.40%。与美国相比,中国数字化媒体与数字化交易对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贡献还存在一定上升空间。
(4)数字经济总产出规模与结构。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及上文对各相关门类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的估算,本文对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产出进行测算,上述年份中国数字经济名义总产出分别为47337.04亿元、65236.80亿元、82769.20亿元、120218.25亿元、147574.05亿元,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产出占当年国内总产出的比重为6.53%。根据BEA(2019)的测算结果,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名义总产出为2.05万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经济名义总产出的比重为6.00%。中国数字经济名义总产出中,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占比最高,数字化交易和数字化媒体占比较小,中国数字经济名义总产出结构变动情况如表5所示。

3.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国际比较
本文对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测算充分借鉴了BEA的方法(Barefoot et al.,2018;BEA,2019)。首先,对数字经济的范围进行界定,在《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中确定数字经济产品;其次,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1)》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确定生产这些产品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最后,通过采用行业增加值结构系数和估计门类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的方法,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加值和总产出等数据进行估算。
研究结果表明,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率显著提升,2017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实际增长率高于GDP实际增长率19.30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加值占GDP的5.73%,2017年占比为6.46%,说明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显著提升。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走势,各组成部分对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贡献中,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贡献水平最高,其次是数字化媒体,最后是数字化交易。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与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产出呈上升的趋势,数字赋权基础设施总产出占数字经济总产出的比重最大,不过其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走势,数字化媒体与数字化交易总产出占数字经济总产出的比重相对较小,然而其比重呈逐渐上升的走势。
现将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模、结构和增长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作比较。在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方面,中国与美国仍存在一定差距,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8.12%,2016年约为美国的52.77%,澳大利亚的6.83倍;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方面,2017年中国低于美国0.44个百分点,2016年低于美国0.77个百分点,与澳大利亚占比相当;在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方面,三个国家占比最高的均为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业;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方面,中国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
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正在快速发展,衍生的新型经济业态和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相比之下,数字经济统计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结合本文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本部分尝试提出一些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核算的建议。
1. 持续推动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主要包含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它们为数字经济运行提供设备支持与技术保障,是数字经济运行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总量指标中,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所占的份额均为最大。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快、规模大,软件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应继续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大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持续推进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加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2. 不断促进数字化媒体与数字化交易产业的发展,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结构
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是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媒体和交易活动融合在一起的产物,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跃迁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度融合,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中的份额逐渐上升。然而,中国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占数字经济相关总量指标的比重与美国相比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应加快完善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机制,加大对相关产业的支持与投入,促进B2B、B2C、平台经济等的发展,提升数字化媒体和数字化交易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份额,优化中国数字经济结构。
3. 及时跟踪国际数字经济测度研究进展,创新数字经济核算方法
与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快且对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统计展开过比较系统研究的国家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统计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为了保障中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结果的国际可比较性,应在理清国际上数字经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明确数字经济的内涵与范围,及时跟踪国际上数字经济测度的前沿研究成果,对国际上不同的数字经济核算方法进行系统对比与梳理,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与特征,制定适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且满足国际可比较性的数字经济核算方法。
4. 加强数字经济统计领域专项问题研究,完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中衍生出许多新产品和新业态,在对数字经济核算整体框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着重研究这类新产品和新业态的核算方法,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核算体系。数字经济拓宽了产品的边界,除货物和服务之外,“数据”和“信息”等无形资产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形资产价值核算对完善数字经济资产负债统计以及数字经济生产统计等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免费”数字内容产品等价值核算对完善GDP核算和数字经济核算体系均具有重要意义。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业态的统计核算研究则可与数字经济统计核算形成良好的互动互补关系,进而加快数字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进程。
5.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探索新型数据采集方法
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是当前有关国际组织、政府统计机构和学者面临的严峻挑战。将传统统计方法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应用于数字经济统计时存在许多不足。国际上已有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如英国统计局等)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爬虫等技术对数字经济统计核算和数字经济数据采集等工作展开了前沿性的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可在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基础上,探索大数据技术在数字经济数据采集领域的应用问题。运用新技术,解决新问题,挖掘新数据价值,不断探索新型数据采集方法。